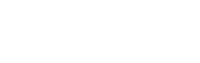行政院日前分别公布促转会正副主委与专兼任委员名单。由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台湾人权促进会及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等多个民间团体共同组成的「监督促转会联盟」旋即透过提问促转会委员,敲钟震虎,希望在就任后选前承诺屡屡跳票、甚至启用具争议性党国旧臣的蔡英文政府不要打假球。
其中,针对张天钦副主委提名人的特别提问,「为了可以继续逮捕匪谍,将前述法网(第68号及80号解释)延伸到14岁以下的第129号解释。……促转会在处理司法平反案件时, 如发现类此的司法解释有违『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可否移请司法院废弃相关解释或判例」,切中了国共内战时期强行征招未成年入伍的史实。据说,当年驻扎在江西宁都一带的少共国际师1万多人,平均年龄只有18岁。年龄最小的红军,更是只有9岁。
虽然当时到底有多少人因适用第129号解释而入狱,不得而知。但这并没有使得这项提问显得无足轻重,相反地,因为它涉及台湾在转型(期)正义的相关讨论中甚少提及的儿童人权,而更值得深入探究。到底儿童在转型(期)正义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可以说,儿童是受害最深,却最晚才获得论及的转型(期)正义相关涉利者。儿童因为年轻,无知,容易受人恫吓,或受家庭经济等压力,而常成为杀害、刑求、绑架,及强迫招募,甚至性暴力的受害者。犹有甚者,由于社会价值规范解体,儿童的加害者不单单来自敌对的阵营,还可能是己方的成员,甚至可能是生命成长历程中的重要他者──家人。这使得还原历史真相,备加不易,他们或是担心受到排挤和污名,或是不忍心让亲人站上刑台,而选择沉默。凡此种种导致武装冲突或军事统治时期,儿童受到的冲击不单侷限在公民政治相关权益,更波及至经济、社会、教育及文化等层面。纵使社会转型,其后续的心理创伤效应,亦可能长达终生之久。
无奈,儿童惯常不被视为是权利的主体,没有发言权,所以,在转型(期)正义的讨论中,一直要到2002年,随着国际刑事法庭的成立,联合国儿童基金(UNICEF)出版了《国际刑事司法及儿童》(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and Children),方才获得正视。
现今普世的共识是,未将儿童纳入转型(期)正义中,不仅违反了《儿童人权公约》,更会严重阻碍社会全面转型的进程。而如何保障儿童也可以参与在转型过程中,获得司法平复,或是咎责,乃至于与自己与社会复和,重建健全、具尊严及信任的人际关系网络,进而促成社会的长远和平,是论及儿童人权与转型(期)正义的学者至为关心的。
咎责?没有错。虽然,一方面,儿童无可避免是受害者,另一方面,更加残酷的事实是,他们未必真的那样无辜。童兵就是个明显的例证。儿童被招募入伍,几几乎是屡见不鲜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国际刑事法庭的《罗马规约》第8(2)(b)条便明定,「征募不满15岁的儿童加入武装部队或集团,或利用他们积极参加敌对行动」犯战争罪。1989年的《儿童人权公约》虽明定未满18岁者为儿童,但却在第38条主张,「缔约国应采取所有可行措施,确保未满15岁之人不会直接参加战斗行为。……在招募年满15岁但未满18岁之人时,应优先考虑年龄最大者。」要到了2002年,公约的附加议定书生效,才规定「各国应尽全力保证15至18岁公民不直接参与任何军事武装活动并不会被迫征召入伍。」
儿童军人,其中有男,也有女。在一些国家,女孩的比例甚至高达百分之25,除了直接参与作战,其职责也包括了照顾伤患、炊事,洗衣,采集食物,有时甚至包括强制婚姻(forced marriage),或性奴隶。正是因为童兵年幼,服从性高,往往轻易犯下令人发指的不人道罪行。过去在转型(期)正义的相关文献中,常常不假思索地将他们直接认定作是「无过失的被动受害者」(faultless passive victim),把女孩刻板印象化为发育不全懵然不知的可怜性奴,男孩则是手持长枪一脸稚嫩的娃娃兵,显然是不正确的作法。
Kieran McEvoy和Kirsten McConnachie 便主张,从1970年代以降,以操弄受害者身分而出现的各式政治动员,采取这样一种「受害者政治」(the politics of victimhood)立场,视加害者与被害者分别隶属二个相互对立的社会范畴,加害者是作为禽兽的「他们」,受害者则是无辜的「我们」。这种二分法在诉求制定政策去保障「受害者人权」并严惩加害者的同时,无形中为受害者形塑了投国所好的刻板印象──「真正的」受害者必须是「无辜的」、必须也「要求严刑重罚」。如果受害者不是这样表现,那他就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某种程度上「算是自作自受」,是「活该的」,自然也无权要求什么法律的正义。
无辜的受害者,当然不是没有,但非常少。要命的是,他们被不当地挪用为集体象征,从而形构出相关的「正邪不两立」的叙事,最终只为了成就我们堂而皇之的居于道德制高点。
偏偏童兵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根本不符合这样的「受害者神话」。实证研究者甚至发现,很难用自愿或是被迫这样简化归因的方式,来描绘受访童兵的真实动机。
与其用对立的范畴来分类转型(期)正义过程中的个人参与,倒不如用光谱或受害者的阶序来形构他们之间的关系。事实是,在转型(期)正义所要处理的结构性罪恶下,绝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是所谓的「坏受害者」,或多或少参与在出卖,或不法利益交换中。Pimo Levi便指出,即便在纳粹的集中营,复杂的权力网络,使得个人无法单单被划为受害者或加害者,特定的犹太人往往被纳粹党卫队指派做监管的工作。曾被囚禁在集中营的意义治疗大师Vicktor Frankl在其回忆录《活出意义来》(Man’s Search for Meaning)称这些人为「酷霸」,不仅常仗势欺压自己的犹太同胞,敲诈勒索,甚至亲自送他们走上黄泉路。相类似的情况,亦出现在南非、狮子山、阿根廷及北爱尔兰等地。
这并不是要否认加害者个人或其群体的可责性,而是让转型(期)正义得以更加接近历史的真相,更能多一些悲悯、少一些报复。也正是因为如此,纵使儿童在转型(期)正义的参与深浅及方式,往往依不同文化脉络而定,但多采取不具备刑事审判意涵的、非以追究罪责为主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及其他复和的传统法律惯习。
由于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或其他的作法,往往由政治势力所操控,2008年由联合国儿童基金及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OGCHR)所举办的工作坊中,一些儿童参与者反对由政客成立委员会来调查真相,并抗议真相为政治目的服务,转而提出使用公开讨论、戏剧、音乐及艺术等形式,来表达儿童的观点,以促进复和。此举或许可以避开法学界对于儿童证词的可信度,以及儿童出席法庭审理会否造成二度伤害,对其日后心理健康影响的相关疑虑。
到底该怎样根据「儿童最佳福祉」来规划转型(期)正义的机制?目前并没有一定的共识。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出于保护的心理,拒绝对儿童进行采证,或容许其出席公听会。但5年之后,2001年,狮子山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却主张,儿童可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中出席作证,惟应在程序上更加保障其隐私。利比亚随后亦采取相同的作法。然而,争议仍旧存在,在肯定儿童的主体性及参与发言权益的同时,如何设立保护性措施,以避免他们处身在超过其年龄所能负荷的心理危机中?转型期的社会像是踩在一条狭窄的红线上,轻易便可能越界,造成儿童的二度伤害,像是在交互诘问时,致令他们经受不住压力,而否认先前作出的证词,或是遭控方逼问,去承认自己杀害或强暴过父母或亲人,抑或是去承担他们无法面对的严厉刑责,进而导致其成功复归社会的希望破灭。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政治的全面转型要能成真,和平与社会重建要能持久,儿童,社会未来的主人翁,理应有份于转型(期)正义。诚如前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主席,己故的南非大主教屠图(Desmond Tutu)所言,「儿童……具有超乎寻常的能力可以洞察事物,可以揭露出事物本来的耻辱和欺瞒。」
传扬论坛期待透过每篇文章激发更多基督徒思考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不断重新理解上主在这个世代的心意。 面对艰困的媒体环境与难以质疑、反省的教会文化,我们没有教派包袱,愿在各个公共议题上与大家一同反思。 为维持平台运作,传扬论坛每个月需要15万元经费,祈请兄姐关心代祷及奉献,与我们同行,并向更多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