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轉型(期)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在台灣所要處理的議題集中在二個時期政府對於人權的侵害上,一是二二八屠殺事件,另一則是白色恐怖。目標則是訴諸對受害者及其家庭的肯認與補償,調查歷史真相,檢討與反省加害者及加害體系。
在簽署二公約後,台灣在2012年進行了第一次國家報告的審查,在〈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24點亦這樣說,「解嚴之前的壓迫與大規模的人權侵犯事件對中華民國(臺灣)社會留下巨大傷痕。政府為了撫平歷史傷口及賠償受害者而採取了某些措施,包括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以及建造二二八事件紀念碑。然而,轉型時期尚未結束,需要政府更多作為來促成中華民國(臺灣)社會的和解。賠償權應包括被害人在社會與心理層面的復原,也應同時賦予追求真相與正義的權利。」
轉型(期)正義,涉及二個要求,一是正義,另一是轉型。可惜一直以來,台灣社會因著藍綠對立,爭議的多半是轉型(期)正義「不正義」的部份,卻很少有人費功夫著墨轉型(期)正義「不轉型」的可能。正是基於轉型(期)正義的推動有可能既不正義又不轉型,不少國外學者開始要求另一種轉型正義(transformative justice),認為即便轉型(期)正義不能完全由轉型正義所取代,轉型(期)正義的理念與作法都必須更朝向轉型正義來發展。
轉型(期)正義有個很清楚的運用脈胳,是「政權變遷後,新政府處前朝政府所遺留下的歷史問題的方式,目的的可能是清算舊政府之不義,或是補償舊政府時期的政治受害者」(Elster 2004)。最早提出這個概念的學者Ruti G. Teitel在《變遷中的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中,提到這樣的一個正義的概念不僅限於傳統法律的框架,涵蓋的範圍可以涉及如刑事正義、歷史正義、補償正義、 政治正義,以及憲法正義等等(Teitel 2000)。
聯合國相關文獻更直陳轉型(期)正義的種種措施必須緊扣著人權及法治來設置,「要協助因衝突所破壞的社會,或協助脫離壓迫政體的社會,重建法治並處理大規模的人權違犯,特別是在一個體制崩毀、資源秏盡、社會安全低落、人們受挫且分歧的處境中,這是艱巨的挑戰。……經驗顯示,要提倡復合及鞏固和平,長期而言,需要建立或重建能有效治理的行政及司法體系,而這些必須建基在尊重法治及人權保障上。」。而轉型(期)正義經常使用的措施包括有: 司法審判,訴說真相,體制改革,以及補償程序等等。
一開始,轉型(期)正義並不打算也不能夠成為處理所有不正義議題的手段,這就是為什麼台灣社會曾經就「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是否納入原住民議題,有過激烈的爭議。支持分開處理者,訴諸的理由是,聯合國《消除一切種族歧視公約》及《原住民族權利宣言》所論及的回復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要求的是,侵略與殖民真相之調查與公開,文化保全與安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平權,以及法主體之建立等,這些都和轉型(期)正義的核心意義並不相同。反對分開處理者,卻以未納入原住民族作為指控政府的「促轉條例」是選擇性正義,難免有政黨惡鬥及挟怨抱復的嫌疑,擔憂在非黑即白的二元仇恨對立中,原住民的相關權益會被犧牲掉。
然而,隨著對轉型(期)正義的修正,轉型(期)正義也逐漸被視為是可以用來處理並未出現轉型期的社會其內部衝突的機制。有學者便進一步依據轉型(期)正義的系譜學研究,將轉型(期)正義的發展劃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且以冷戰時代的出現告終,這期間轉型(期)正義被看作是例外的、跨國性的措施。第二個時期是1989年以後後冷戰時期,隨著不少國家民主化及現代化的出現,轉型(期)正義是連同不同的社會處境及法律來進行論述的。第三個時期則是在二十世紀末出現,針對全球化所帶來的政治不穩定及暴力的正常化現象,來談轉型(期)正義,亦是所謂的「穩定時期的轉型(期)正義」(steady phase of transitional justice)。於是轉型(期)正義不再被視為是一種例外,抑或是某種過渡階段的作法,而是一種常態,最明顯的例證便是伴隨著國際人道法的崛起而成為聯合國常設組織的「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的出現(Teitel 2003)。在這個意義下,「轉型(期)正義」意味著的僅僅是,帶有某種工具性的價值,其目的在促成某種政治上轉變的,針對特殊的、一定時間範圍內的某種形式的正義。
轉型中的轉型(期)正義
截至目前為止,轉型(期)正義在世界各地的實施,一般來說,成效和影響都不明確,甚至是令人失望的,受批評的,或被譏為「成功者的正義」,或是認為頂多能「治標而無法治本」。
學者Paul Gready and Simon Robins在〈From Tansitional To Transformative Justice: A New Agenda for Practice〉一文中便批評轉型(期)定義受到二種類型的限制,一是基本的,另一是次級的。基本的限制指的是自由主義式的和平理念,以及由上而下的以政府為主的進路。至於次級的限制,則主要是由基本限制所導出的「離地的」實施措施,以致於未能促進社會真正的轉變。
自由主義的和平理念主要是受到二種全球化的影響而形塑的,一是自由主義有關於公民及政治權利的典範,因而強調選舉、程序民主,立憲主義,法律的治理,以及諸多向後回顧的確之真相與正義的措施。另一則是則是由市場所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以及所謂「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干預措施。
上述的作法,偏好在脆弱的轉型期處境中,優先創設一些機構,而不是用更具脈絡的方式來促進大眾的福祉,這招致了不少批評。到底何謂「脆弱的轉型期處境」?根據2011年的「新方案」(New Deal) 是這樣界定的,「缺乏能力或意願去逐步促進公民共同的發展,並且特別容易因外在的動盪及內部的衝突而受挫。」雖然有了新機構,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最終在運作上被架空,而無能積極回應公民社會的真正需求。因此,在處理過往的不正義時,轉型(期)正義過於關注加害者個人或政府的暴力,卻無法處理結構性的暴力及不平等的社會關係。
由上而下的國家主導進路則往往侷限在跨國的菁英階層,以及國際援助上,因而採取的策略進程,往往是失根的,受外界所主導的,在具體的實施措施上,亦往往缺乏在地化,沒有或缺少本地的聲音,進而無法進一步發展出本地的草根運動。縱使有諸多宣稱可以賦權的作法,都因為缺乏受害者的直接參與,使得發言權被轉型(期)正義的非政府組織所把持,受害者不得不依附於這些組織下,任令其為他們代言。轉型(期)正義在作法及理念上應更具轉型正義。
究竟何謂轉型正義?簡單來說,這係以轉型(期)正義作為對立物所得出的,「轉型正義並不尋求完全取消或取代轉型(期)正義,但它確實企圖徹底地改革它的政治、位置及優先順序。轉型正義意味著焦點的轉移,從法律到社會及政治,並且從政府及機構轉到社群及日常的關切。轉型正義並不是一個外在法律的架構或是機構的模型由上而下的結果,而是一個由人們的需要及生命的分析和理解出發,由下而上的過程。與之相似,轉型正義的工具不會侷限在轉型(期)正義的法庭及真相委員會,而會由能夠影響更多涉利者的社會、政治及經濟的政策及措施來組成。」
從性別和原住民這些在轉型(期)正義中較少被觸及的領域為例,便可以看出促使轉型(期)正義進一步轉型的重要性。
性別與轉型正義
有關於戰爭的質性和量化研究均顯示,戰爭是高度性別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傷亡的人百分之八十是軍人,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只有近半是。當越戰時,只有百分之二十是軍人。其他的全是平民,其中最主要是婦女和孩童。性別暴力往往更常出現在內戰中,以刻意羞辱對戰的另一方男性無法保障自己族群的女性。
Richard Payner、J. Pettman及R. Rayner等人更主張,軍事訓練涉及高度男性氣概的社會化歷程。年輕的士兵往往透過與娘娘腔等陰性特質的切割,來證明自己是個好軍人。這往往涉及對年青男人在性方面的不安全感及性身分認同來達成。與性侵害極其相關的男性迷思,特別是性角色扮演的刻版印象,同對女人的敵意,或對性暴力的認同與接納,便在這個過程中建立起來。
可惜的是,專門內來處理後衝突的轉型(期)正義,不論是司法審判,抑或是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卻因為採取某種性別中立的立場,而往往無法全面地呈現婦女人權的大規模侵害現象。紐倫堡及東京戰犯法庭完全未提及戰爭中的強暴及慰安婦等議題,便是一例。這個情況一直要到在1990年代以降,跨國女性主義者開始關切衝突中性暴力的法律處置議題,才獲得改善。
國際社會相關法律的改變,主要在三方面: 首先,要確認婦女在武裝衝突中所遭受的性別暴力被列為嚴重的戰爭罪行名單中,這意味著,將性犯罪視為是違反人類罪行,種族滅絕,更是對日內瓦條約(Geneva Conventions)的嚴重背離。國際刑事法庭更明確將強暴、性奴隸、強迫援交,懷孕、絕孕以及其他的性暴力視為是戰爭罪,人口販賣亦被包括在違反人類的罪行中。其次,是協調這類型的戰爭罪行在法律標準與起訴實務上的落差,這主要是在檢討有關於戰爭罪行該如何進行調查,以及可以援引哪些條例來徵詢專家意見等等。最後,推動法庭審理程序的改革,避免對受害者造成二度傷害,包括調整證據法則,禁止使用受害者過去的性行為作為佐證,取消對受害者證詞的查核,以及限制使用知情同意作為性侵害辯護的理由等等。
無奈的是,法庭審理之外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乃至相關的補償條例等機制,經常亦是假借著某種性別中立的立場,有意無意將婦女排除在外。這導致在戰爭後對婦女的父權打壓往往再次復辟,在有關於政府如何轉型,以及轉型成為怎樣的社會的過程中,婦女往往遭到排擠。
後來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機制因而採取了三種修正的作法,以便讓其更具有轉型正義,像是採用性別主流化的理念在所有的運作上,從相關人員的培訓到招募等,或是成立特別的單位主要來負責性別相關議題,作出報告,並進行具性別正義視角的分析與判讀,或是結合上述二者的折衷作法。
被拿來和智利及阿根廷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來作對比,視為是某種具性別平等指標的南非,就針對性暴力的受害者採取了比較特殊的安排,諸如: 容許他們不必公開作證,證詞也保密,在清一色女性或由婦女團體所組成的、不對外公開的聽證會作證。其實,這在當地的女性主義者眼中,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像是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過窄地定義對人權的侵犯在對個人公民及政治權利上,特赦的相關要件很難適用在性侵害案件中,以及一開始未能根據性侵害事實常導致受害方遭到排擠與污名化的社會文化脈絡,設計出對受害者友善的審理環境,凡此種種導致受害者不敢述說,加害的男性無誘因認罪,乃至社會父權意識越發地根深蒂固的情況。
猶有甚者,在黑白嚴重對立的氛圍下,不少黑人女性遭受到的性暴力其實不單來自白人,也有不少來自自己黑人「非洲國民議會」(ANC)的同志。不少黑人女性噤聲,或是害怕揭露自己的遭遇,會被視為是背叛出賣,被自己所屬的政黨及族群排斥,或是擔憂如今己上位的加害者會對她們採取報復性作為,或是害怕在父權的社會氛圍下,加害者非但無法遭定罪,自己反倒毀了從政生涯的未來。
在這樣的情況下,Rita Mazibuko的遭遇變成了沈默文化規訓不聽話的女性絕佳的範例。Rita Mazibuko曾在流亡時遭到多位ANC同志的性侵,並獲得另一些男同志如Mathews Phosa的幫忙。但當時任省長的Mathews Phosa勸她不要出來作證,否則他會為了捍衛ANC的緣故,否認這件事。不顧勸阻的Rita Mazibuko離開證言台時,是挫敗的,一位學者這樣描述,「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她控訴時不發一言。沒有一個委員,甚至沒有一個捍衛女權的女性主義者,站起來說,『我們尊重Rita Mazibuko 按著自己所知的述說的事實,正如我們尊重Mathews Phosa的一樣。但我們期待他也能出來作證。』」
原住民與轉型正義
正當轉型(期)正義逐漸擴及其他未經歷轉型期的社會,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補償等機制,被用來處理大規模的人權違犯事件,不知不覺地將西方自由主義下的民主社會視為可欲的標的,轉型(期)正義「卻忽略了所謂的自由主義民主本身,也需要在後衝突的復和與修復式正義的框架下,加以審視」。
因而,嘗試用轉型(期)正義來處理原住民正義的訴求,往往會在三個面向上遇到政府與原住民社群的衝突,轉型(期)正義本身不但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甚至成為政治爭端。首先,究竟轉型(期)正義要處理的時間起迄點如何界定。其次,政府可能訴諸歷史及當前合法政策來劃定轉型(期)正義的合理界線,而原住民社群卻想要用過去來批判現今的政策。第三,政府會意圖使用轉型(期)正義來確認主權與法律正當性,但原住民社群卻會抗拒這樣的策略,甚至作出不同的有關於主權及法律正當性的宣稱。
不過,近來在實務上,隨著加拿大及澳洲政府嘗試以轉型(期)正義來解決原住民人權爭議,不少原住民社群在爭取原住民人權的訴求時,也開始有條件訴諸轉型(期)正義的法律框架。所謂的有條件,一方面是帶著高度文化敏感度的,特別是針對轉型(期)正義往往會強化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典範這點,另一方面是爭取主導權,以便用更具轉型正義的作法,比如說在個人人權之外,要求像是自治、土地等集體權利,來修正轉型(期)正義。
Jennifer Balint, Julie Evans and Nesam Mcmillan等學者便受到諸如女性主義轉型(期)正義理論的影響,一方面,用結構性不義來界定殖民歷史帶來的傷害,一方面引用Iris Marion Young的理論,要求轉型(期)正義應該超越對加害者個人或政府的究責與補償作法,更深入分析歷史創傷所帶來的結構性不平等後果,並對更深層的、範圍更大的改革,抱持開放的態度,甚至考慮納入原住民傳統司法,來全面促進社會、政治、法律乃至經濟的轉型。
以土地為例。原住民族其實肯認他們祖先的土地如今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和他人共享,只是這樣的共享必須是建基在平等的基礎上。由於土地對原住民文化傳統及族群的延續至關重要,而移民往往對原住民族群的生計造成非常大的影響,因此,必須對相關的開發作出限制。當然,對於怎樣才構成平等基礎,原住民與移民有不同的界定,需要作出更多的協商。而協商就住一步涉及到雙方不同的期待。由於原住民族土地的歸還,伴隨著的是期望得以維持原住民自治,所以土地不是單單歸還給個別的所有權人,更要考慮到族群如何在成員個人及群體的權利與義務間達到某種平衡。這使得引入原住民傳統司法,顯得更加重要。
教會可以扮演的角色
台灣有關於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雖然不缺女性,但卻多以受害者家屬的身分被記憶。婦女是否因為結構的不義而遭到性侵害,或淪為社會經濟的弱勢?性別該如何納入轉型正義的機制中,落實一個具性別公義的新國家?
另一方面,蔡英文總統就任後,曾代表國家為歷代殖民政權迫害族人和土地流失,向台灣的原住民族道歉,並宣示總統府將設置「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來推動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不料,去年2月14日由原民會公告的「劃設辦法」,因考量到憲法保障私有財產權,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中現今的私有地排除在外,讓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硬生生少掉近百萬公頃。原住民族為此強烈抗議,在凱道上露宿至今,抗爭猶在持續中。如何讓轉型(期)正義在性別和族群的議題上真正發揮轉型效應,這些問題的探討,在台灣猶在起步階段。
教會,做為台灣社會的一份子,在強調在地化、由下而上的深層轉化的轉型正義中,理應能夠扮演更形重要的角色。舉例來說,社群權責(Community accountability),便是以社群團體(朋友、家族、職場、鄰舍,包括教會在內)為中心所發展出的一種轉型正義的策略,旨在讓社群被組織和動員起來,去促成幾件事: 首先,創造並肯認相互支持及關懷的社群價值,並且拒絕侵害和壓迫,進而,採取積極作為,提供受暴力攻擊的社群成員安全及支持的網絡,並尊重他們的自主決定,再進一步發展出長期的策略去對治社群加害者的惡行,讓他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並加以轉化,最終,落實社群的政治結構的翻轉。然而,要推動社會轉型正義的教會,必須從自身做起,先從內部的轉型開始,真誠面對過往與威權體制的歷史,現存的性別及族群歧視,以及教會政治中未盡民主的代議結構。
(Photo credit: Nomad@Live / CC BY-NC-ND)
傳揚論壇期待透過每篇文章激發更多基督徒思考信仰與社會的關係,不斷重新理解上主在這個世代的心意。 面對艱困的媒體環境與難以質疑、反省的教會文化,我們沒有教派包袱,願在各個公共議題上與大家一同反思。 為維持平台運作,傳揚論壇每個月需要15萬元經費,祈請兄姐關心代禱及奉獻,與我們同行,並向更多人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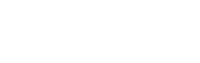
除非全然更新,所謂革命,也就是轉型正義。否則政黨輪替只是新瓶裝舊酒,綠正義取代藍正義,政權轉移換人享受權力而已,本質毫無變化,只是多了轉型期正義的「改革」把戲,下回2020政黨若再次輪替,換人抬出轉型期正義報復性的「改革」。無論性別、種族、勞工、貧富或新生代前途等等問題都成「改革」戲碼。街頭抗爭成為台灣自由、民主、人權的觀光特色。
總之壞樹結不出好果子。有誰能把台灣這欉番薯重新換種好種?纔是所有住在台灣的人之期待。至於教會若不重生,權力之酵不除,有能力的基督徒若不從政,教會仍是無可救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