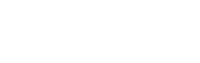在美国生活的华人中产阶级,大都居住在经济最发达、文化最多元的东西两岸以及新兴产业增长强劲的德克萨斯州。他们未必能融入主流社会,分享由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和犹太人所垄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但身为拥有高学历的专业人士(一般都充当软体工程师),即自我调侃的「码农」,至少获取较高薪水、过著富裕的中产阶级生活,并为下一代提供优越的教育条件。这群华人白领,跟杰德.凡斯这种自称「乡巴佬」的、身处中部地带的「另类白人」宛如生活在两个美国,他们无法想像杰德.凡斯(J. D. Vance)在自传《绝望者之歌》中描绘的乡巴佬生活状貌。只到过东西两岸「精华地带」的华人旅行者和留学生,更不知道还有杰德.凡斯笔下的另一个美国和另一群美国人。
以族裔和阶级身分而论,杰德.凡斯自我界定说:
我虽是白人,却属于美国数百万「苏格兰—爱尔兰」裔的劳工阶级。对于这些家伙而言,贫穷是家族传统,他们的祖先是南方奴隶经济体系中的临时工,之后成为佃农, 再成为煤矿工,近年来又成为机械技师和磨坊工人。美国人称他们为乡巴佬、红脖老粗及白人垃圾,但我称他们为邻居、朋友及家人。
经济和阶级地位的差异,大于种族的差异。某些白人与另一些白人之间的差异, 大于某些白人与某些华人及其他人种之间的差异。就地理环境而言,这类乡巴佬生活在大阿帕拉契山脉地带,深受阿帕拉契亚大山谷文化的影响。这个区域很大,从南部的阿拉巴马州一路延伸到乔治亚州,再往北直到俄亥俄州及纽约部分地区。他们长期自我封闭、自给自足,却在二十世纪末期这场无远弗届的全球化浪潮中,如同滚筒洗衣机中飞舞的泡沫般身不由己、前途莫测。整个工业链条迅速繁荣,又更加迅速地衰败,他们猝不及防,梦想幻灭、家庭破碎、生命断裂。
新自由主义预言全球化带来世界大同,但长期以来这群乡巴佬被东西两岸的主流社会和菁英阶层遗忘、背叛、蔑视,光鲜的美国梦跟他们毫无关系。东西两岸愈是亮丽,中南部就愈是黯淡,两者的「反向命运」存在着草蛇灰线般的关联性。左派牢牢掌控的媒体和顶尖学术机构,联合封杀乡巴佬的声音;「政治正确」的紧箍咒,又让他们只能「沉默是金」。欧巴马在谈起中西部小镇上的失业人士时轻蔑地说:「那里的工作已经流失25年了,没有新的工作出现,这群人变得忿忿不平也不足为奇。于是他们依恋枪枝或是基督教,或者对与他们肤色不同的人感到反感,或通过反移民和反贸易的情绪,来表达他们的挫折。」这种居高临下、带有侮辱性的说法,似乎是说,你们的失败都是你们自己的错。这种说法让美国工农大众更加愤怒,他们于是成为川普的强烈支持者。
「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当川普在一场激烈的大选中捕捉到他们的心声并毫不隐讳地替他们说出来时,他们的愤怒如决堤的大洪水,「惊涛拍岸,乱石穿空,卷起千堆雪」,成为一股将川普这个「非典型」政治人物推进白宫的重要力量。欧巴马执政八年,将政治钟摆摆到罗斯福新政以来左翼的最高点,美国的传统价值和立国根基遭遇前所未有的侵蚀。如今,政治钟摆猛烈往回摆动,这是不是乡巴佬们所期盼的福音呢?
他们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受害者
杰德.凡斯的家族来自东肯塔基州的山区,是「苏格兰-爱尔兰」裔的白人移民,从东岸平地来到山里谋生,定居在此。这里曾因伐木业及矿业发展出繁华小城,二十世纪初政府开始保护阿帕拉契山林木,加上煤矿业没落,广大居民失去工作机会,经济及社区发展一蹶不振。
随着二十世纪上半叶钢铁、汽车等工业兴起,乡巴佬们移居平原地区的新兴工业城市,成为大型工厂中里的工人。他们享受到城市化的荣景,拥有现代化住宅、稳定的收入、水准不错的公立学校,美国梦似乎近在咫尺。谁也不曾料到,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美国的钢铁和汽车等工业显现疲态,工厂纷纷离开美国,老板去人力成本更低的亚洲或南美开新厂。正要蜕变为城里人的乡巴佬们,在地图上连中国都找不到,却被中国从未谋面的农民工夺去工作机会。乡巴佬们不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是全球化的牺牲品——虽然他们与普通的美国消费者一样, 可以在沃尔玛等超级市场买到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但他们失去了工作,也就失去了消费能力,他们失去的比得到的多得多。当然,这些夹在乡巴佬和城里人之间身分暧昧的美国劳工,境况并未糟糕到中国沿海劳动密集型工厂里不堪压力跳楼自杀的农民工的地步,但他们被锁定在日渐衰败的城市中、找不到新的工作机会、公立学校水准不断下降、家庭破碎、暴力及毒品泛滥,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他们的希望逐渐破灭, 被绝望所笼罩。
这就是杰德.凡斯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他的母亲是从山区移居城市的第二代工人子女,她原本是一位优秀高中毕业生,还被选为毕业致词的代表,大有希望进入大学学习,却未婚先孕、生下孩子,失去以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契机,人生轨迹直线下坠。在凡斯的成长过程中,他的母亲至少换了16位男友,他至少有过五个继父。丧失自控能力的母亲,沉溺于药物和毒品,失去医院护理师的工作,成为被孩子照顾的对象。像凡斯母亲这样的「人生失败者」,在其亲友和邻里之中比比皆是。外部环境的恶化和内心的崩塌,使他们无力改变命运。更可怕的是,第三代的孩子大都愤世嫉俗,认为「我再怎么努力也没用」,自暴自弃、自取灭亡。
东西两岸的菁英阶层对乡巴佬群体视而不见。他们倒是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股票扶摇直上的矽谷高科技企业、华尔街的投资者和律师、华盛顿的政客和游说者、好莱坞的明星,这些人「理所当然」地成为美国的「脸面」。殊不知,美国的「里子」却在溃败和腐烂。
深入研究2016美国大选的外商资深策略顾问叶立锜撰文分析说,欧巴马任内的政策如减碳、发展绿能以降低暖化速度,立意看似良善,但势必降低化石燃料使用、增加营运成本甚至关闭工厂。自由贸易协定(FTA)虽有助全球化与加强与盟邦互惠,却会伴随「去工业化」及工厂移出,这些政策受害最深的是中西部各州的乡村小镇,以及在全球化下工厂大量关门的铁锈带——密西根、俄亥俄、宾州等州。美国不分政党,三位总统柯林顿、小布希到欧巴马,都是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蓝领与中产的反体制忿怨,让川普在共和党党内初选阶段轻松击败以体制派为主的十六位参选者。
川普是极少数体察到乡巴佬的愤怒和痛苦的政治人物,他在总统就职演讲中说: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首都的一小批人从政府获得好处,而买单的是人民。华盛顿繁荣了,但人民却没有分到好处。政客发达了,但是工作流失了,工厂关闭了。既得利益集团照顾了自己,但是没有保护我国公民。他们的胜利没有成为你们的胜利。他们的成功没有成为你们的成功。母亲和孩子陷于市区的贫困当中,废弃的工厂像墓碑一样遍布全国各地,教育系统资金充足,而我们年轻可爱的学生却无法获得知识,犯罪、帮派和毒品夺走了太多的生命,也夺走了我们国家太多未能发挥的潜力。
川普上台之后确实扭转了这种「只让东西两岸菁英受益」的全球化趋势,透过重新签署与外国的贸易协定,让更多的工厂和工作机会转移回美国。
他们为什么从民主党人变成共和党人?
凡斯靠个人奋斗以及好运气,摆脱了乡巴佬的厄运。当他跻身于从常春籐名校毕业的「高等美国人」行列之时,也沾染上波士顿、纽约和矽谷的「政治正确」,他是共和党人,2016年却没有投票给川普;他的那些仍在铁锈地带等死的乡亲们,听到川普的讲话,热血沸腾、心有戚戚焉,都是川普的热切支持者——传统的媒体不愿倾听乡巴佬们的心声,不会料到川普具有如此强大的民意基础,在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
书中最发人深省的部分,是作者分析这群乡巴佬,如何从「坚定的民主党人」转化成「坚定的共和党人」,甚至因为传统共和党人向中间立场靠拢,转而选择坚持更草根、更坚持共和党基本价值的川普。川普与希拉蕊的对决,铁锈地带的几个中部州的翻盘,至为关键。威斯康辛、密西根、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等州,向来是民主党的铁票仓,民主党认为工人和工会必然支持他们——希拉蕊从未去过这些地方催票。选票开出来之后,这些州全都由蓝转红,民主党那些满口仁义道德、满肚男盗女娼的政客悔之晚矣。
为何不到一个世代的时间,阿帕拉契山区及其南侧区域会从民主党支持者转变为共和党支持者?有人从种族和宗教的原因来解释——白人和基督徒更愿意投票给川普。凡斯的回答却是:比贫富悬殊和种族差异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对乡巴佬的忽视和蔑视,终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们是贫穷的乡巴佬,但持守自己的尊严,可以忍受贫穷,却不能忍受政府和菁英对其尊严的剥夺。民主党政府偏好于施行「帮助穷人」的福利制度,反倒点燃穷人的怒火——这套制度是在剥夺乡巴佬所剩无几的尊严。过去美国人可以不用每年花数万美金取得大学学历,在家乡附近镇上一家小公司或小工厂找份正常工作即可过活。在全球化后,美国本土制造业没有竞争优势,非知识工作者多数只能做没有员工福利的兼职工作,领着微薄时薪,「这群人要缴上个月的电费都很困难,怎么会想到绿能、全球暖化跟自由贸易」。愈来愈贵的欧巴马健保,看着欧巴马政府花大钱保护中美和中东难民,社会贫富差距愈来愈大,他们当然转而投票给川普——「铁锈带」的蓝领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让工厂与工作机会移至墨西哥、世界贸易组织(WTO)导致大量中国商品进入美国等结果极度不满,选民统统都在2016年宣泄在选票上。铁锈地带的钢铁工人约翰告诉媒体,自己一直是民主党支持者,但因为川普竞选时对钢铁行业的承诺,而改投共和党一票。
欧巴马把自己打扮成穷人总统、平民总统,但乡巴佬们对其极为痛恨。凡斯用充满讽刺的笔调写道:
欧巴马的出现立刻引发我们最深刻的不安全感:他是个好父亲,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他上班穿西装,我们穿连身工作服(首先我们还得想办法找到工作);他的妻子告诉大家不该喂小孩吃某些食物,我们恨透她这么做——不是因为她说错了,而是我们知道她说得没错。
欧巴马推动的那些所谓进步价值,更是让乡巴佬们怒火中烧。乡巴佬们举双手赞同川普对欧巴马的批评:「大家都知道我不喜欢欧巴马总统,我认为他是个很糟糕的总统——他没经验又自大,把我们国家给害惨了。」
如何找回美国的清教徒传统?
凡斯价值观的转变,发生在十七岁那年。外婆为了让他明白金钱来之不易,让他假期到百货公司兼职当收银员。正是在收银员这个卑微的职位上,凡斯看到了决定社会政策的菁英们在办公室中看不到的人间百态。他发现,很多所谓的穷人,挖空心思钻福利制度的漏洞,分批结帐,用食物券买食物,再以折扣价卖出换现金,最后用现金购买啤酒、葡萄酒和香烟等奢侈品。这整个过程都在他眼皮子底下施施然地发生, 他无权制止,也无法举报。
凡斯的外婆苦口婆心地教育他说,一定要努力工作、不能不劳而获,尽力不要成为领取政府福利的人。然而,在民主党的社会政策之下,勤劳工作者得不到尊重和保障,偷奸耍滑者反倒游刃有余。凡斯举例说明福利制度带来的不公:「每隔两周我会收到微薄的薪资支票,然后注意到联邦政府会从薪资中扣掉所得税。在此同时,一位住在附近的用药上瘾者也会以差不多的频率来买丁骨牛排。我穷到买不起丁骨牛排,但托山姆大叔的福,我得替其他人买的丁骨牛排结帐。」他心里非常愤怒:「我实在搞不懂,我们家辛苦度日,这种人却可以靠福利津贴享受这些我完全没有机会尝试的小玩意。」凡斯得出结论:民主党号称代表工人,其实言行不一。
《绝望者之歌》最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在质疑左翼世俗主义思潮的同时,也对当下美国教会做出深刻反思。凡斯指出,与一般人刻板的印象相反,大阿帕拉契山区会上教堂的人比中西部、西部山区及密西根州与蒙大拿州之间的人还要少。「在我出生的俄亥俄州南部,辛辛那堤和代顿这样的大都会区其实很少有人上教堂,比例大概跟极度自由开放的旧金山差不多。」但在接受民调时,基于对传统的尊重,大家都说谎,声称每个礼拜日都去教堂,因而造成「圣经带」信仰稳固且繁荣之假象。实际上,在铁锈地带,宗教机构虽然帮助许多人维持稳定的生活,但面对制造业衰败、失业率高企和滥用药物等严重问题,教堂已然无能为力,信徒大量流失。
如果该地区的信仰真的稳固而鲜活,凡斯的外公怎么会酗酒并死在外面?凡斯的母亲怎么会一次次婚姻破裂并染上毒瘾?遗憾的是,教会的神学和讲道刻意回避信徒的现实困境。凡斯的外婆是虔诚的基督徒,却极少去教堂做礼拜,她发现教堂里的牧师在讲台上「耍蛇」——这不是一个比喻,极端灵恩派教会确实如此,他们像杂技团的艺人那样耍蛇,似乎表明其拥有旧约时代先知摩西的能力。凡斯的外婆是乡巴佬之一员,从未受过高等教育,不具备强大的理性精神,她凭借长年在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常识,对极端灵恩派的作法不屑一顾。确实,无论牧师耍蛇的本事有多高,只能让人拍案惊奇,但无法带来广大信徒信仰的复兴。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新教各宗派中,美国灵恩派教会信徒数量的增长最快,但并未带来从政府政策到家庭婚姻的整体性的翻转。
在高中时,凡斯跟生父短暂相处了一段时间。他的生父常去教堂,也带他一起去,打下他的信仰根基。在敏感多思的青少年时代,凡斯观察到教会的种种情形,不能让人点头称善。很多基督徒的言行不具基督徒精神,整天如惊弓之鸟,忧心忡忡、患得患失——担心世俗资讯洗脑年轻人、担心艺术装置污辱信仰、担心菁英迫害让世界成为恐怖而陌生的国度。牧师在讲台上攻击同性恋将导致世界末日、地球毁灭,却很少宣讲基督徒应有的美德,「我所学到的基督徒的道德观,反而呈现在消极反对他们不接受的主张,譬如同性恋议题、进化论、柯林顿的自由主义或者婚外性行为。」 这种视野和思想被狭窄化的、处于防御状态的基督信仰,丧失了基督信仰的精髓。
今天,无论美国教会还是美国社会,都应谦卑地追寻建国之初的清教徒传统,从中发掘医治「美国病」的药方。历史学者霍尔在《改革中的人民:清教与新英格兰公共生活的转型》一书中指出:
我们是否正确理解了清教徒为什么如此重要?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它很重要,是因为我们的公民社会和他们的公共生活一样,有赖于把权力的使用和公益的道德联系起来。在我们这个社会,自由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人们过于关注权利而忽视了对整个社会的义务和责任。权力被滥用、公益缺乏的现象随处可见。正确理解清教徒不会改变我们在感恩节吃什么,但是可能会改变我们感恩的对象和内容,可能改变我们想像更好的美国的方式。
作者:余杰
本文出自:《川普向右,习近平向左》

传扬论坛期待透过每篇文章激发更多基督徒思考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不断重新理解上主在这个世代的心意。 面对艰困的媒体环境与难以质疑、反省的教会文化,我们没有教派包袱,愿在各个公共议题上与大家一同反思。 为维持平台运作,传扬论坛每个月需要15万元经费,祈请兄姐关心代祷及奉献,与我们同行,并向更多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