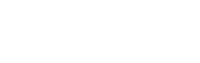近年來,社會越來越留意靈性(spirituality)與政治生活的關係。這是一件好事,因為靈性不再被視為只屬於宗教、唯心和個人的事。然而,當下處理靈性與政治生活關係多傾向將靈性安放在個人身上,並從中探討靈性對從政人和社會運動者的影響。
這類研究的不足之處,就是未能展現出靈性本身的政治向度。這篇短文嘗試用亞美(Sarah Ahmed)提出的「情緒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概念思考靈性與政治生活的關係。
情緒的文化政治
簡單來說,情緒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指情緒的社會性。它屬於一種社會和文化實踐多於一種個人心理狀態,即情緒的文化政治是社會建構,並由此塑造我們對事物的解讀,引導我們傾向它期望我們要有的某種反應和行為。
這些反應和行為是反射式(reactive),不是主動式;倚賴式,不是自主式。有別於論述,情緒的文化政治以挑動和強化我們最原始的情緒為主(例如,受威嚇、憎恨、痛苦、厭惡和愛的情緒)。因情緒屬於第一層次活動,它比理性對個人的影響更直接、更快,甚至更深刻。
情緒的文化政治多數由管治階層藉著某一事物或事件製造出來,透過不同媒體和活動,滲入個人生活,以致令人們產生相近的情緒。結果,管治階層製造的情緒不但得以被提昇和被放大,甚至成為維繫社會要素之一。
在情緒的文化政治下,情緒是個人與社會之間溝通的媒體,而不是理性和理念。有別於感受(feeling),情緒的文化政治的核心不是個人對某一事物或事件的不同感覺,而是情緒的文化政治的目的是甚麼、為誰服務、要達到甚麼管治目的。
情緒的文化政治是任何一個政府或管治者常用的方法。例如,前南非白人政府在阿非利卡人(Afrikaners)中製造對黑人憎恨的情緒(黑人是次等,並威脅白人的安全)、美國政府在911事件後在美國人中製造對穆斯林恐懼的情緒(穆斯林是野蠻和暴力)、中國政府在中國人中製造以黨國為核心的愛國情緒。
香港政府也不例外。1999年,香港政府以若不修改《基本法》對居港權的界定,於未來10年,將有167萬人從中國到香港定居,香港將陸沉。香港政府製造受威脅的情緒,而最終,大部份香港人對修改《基本法》行動沒有異議。
另一例子,自香港經歷亞洲金融風暴和SARS,香港政府利用獅子山下的故事塑造一種面對逆境的文化政治,鼓勵香港人。但實際上,政府藉此要打造向北望文化(因為宣傳片的獅子山是從九龍向北望)、不埋怨政府的忍耐和「肯捱」的態度。
然而,這十多年來,部份香港人對於政府帶有政治目的製造出來的情緒文化政治越來越不為所動。例如,部份香港人對於以經濟發展作為情緒的文化政治不為所動,反而以批判眼光看待高鐵興建、新界東北和大嶼山發展、港珠澳大橋和自由行。在覺醒之餘,我們是否也可能陷入韋伯(Max Weber)所說的,即從解魅進入另一著魅?
恐懼被動的文化政治
當政府管治越來越專橫和野蠻,而一般的抗爭行動沒有帶來實質轉變時,有部份人對被動也恐懼起來。被動被視為是弱者的表現、容許被決定和被擺佈,而最終被動使我們失去自己、坐以待斃。
在恐懼被動的文化政治下,抗爭者刻意要反被動、反軟弱、反被擺佈,而行動就成為恐懼被動的文化政治之態度。以今年年初一和年初二凌晨警民衝突事件為例,擲磚頭者認為這是官迫民反的結果,擲磚頭是拒絕被動和表達自主的行動。
在《給港人的最後錄音》,本土民主前線黃台仰說「寧為玉碎 不作瓦全」,以行動拒絕被動。專欄作家李怡說:「香港人必須認識到我們面對的政治環境,昇平時世已過去,抗爭時代來臨,不能再以舊日的太平心態去看待街頭衝突。」
在恐懼被動的文化政治下,人若不願做港豬(形容一些香港人不關心時事政治,崇尚玩樂和只顧自己,懶理不公義的事),就要站出來,用行動拒絕被動。然而,行動需要以不斷升級克服對被動的恐懼。
雖然「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也是一種拒絕被動的行動,但在強烈恐懼被動的文化政治下,「和理非非」被批評為被動和左膠,因為他們仍在認同秩序的文化政治下生活。擲磚頭是自主的表現,甚至拒絕為所做的負責任是公義的表現。
我承認不是一切抗爭的行動都是源自恐懼被動的文化政治。那麼,當下抗爭行動是覺醒的結果還是受恐懼被動的文化政治主導?當下抗爭行動是否喚醒睡著的人還是強化秩序和恐懼被動的文化政治?若情緒的文化政治特質之一是製造威脅的他者,當下抗爭是否也製造威脅的他者,並將自己受害化?
靈性、情緒、理性
理性往往被視為對情緒有效的控制,但這種以理性控制情緒的思維犯了一個基本性毛病。即理性不是對立於情緒,理性更不必然優於情緒,因為理性也要回答那一種理性和誰人的理性。再者,理性可能是由情緒建構出來。
那麼,在情與理外,政治生活需要靈性,作協調和整合。靈性是邁向他者,對比自身還要高的真善美之體驗和嚮往,並從中產生促進萬物間的公義和仁愛的價值、態度和生活實踐。這使我想起一個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希特勒大軍攻陷丹麥時,他強迫丹麥國王下一昭書,命令丹麥境內所有的猶太人戴上繡有達味(大衛)之星的黃臂章。丹麥國王知道希特勒的詭計是要將這些猶太人送往死亡集中營,然而他也知道違逆希特勒的後果將是多麼地可怕,於是在下達昭書的同時,他先在自己的手臂上戴上了黃臂章,當所有的百姓看到國王的行動時,他們便知道了國王的用意,因此也都紛紛地戴上了黃臂章,於是乎,全國上下,不論是猶太人或是丹麥人,每一個人的手臂上都戴上了相同的黃臂章。這位丹麥國王為了拯救猶太人,冒普生命危險,戴上了黃臂章,而其人民也跟從了。
我曾跟丹麥朋友確認這事的真實性,但其回覆是,歷史沒有這記錄。然而,他寫,「雖是如此,但若真有這事發生,我們丹麥人的回應會跟這故事一樣。」(事實上,在拯救猶太人一事上,丹麥人民是佼佼者。)這故事表達出一份在情緒與理性以外的靈性,一份願意為他者犧牲的精神。這份靈性不只是少數人擁有,更成為這國家的文化。
靈性是私人的,但不是個人(private, but not individual)。因此,靈性也是群體文化。事實上,沒有群體文化向度的靈性,私人的靈性難以培育。那麼,跟隨的課題是:1.那些群體能培育靈性?2.他們培育甚麼的靈性?3.這些靈性跟政治生活有甚麼關係?4.他們如何跟一個情緒的文化政治對話?
教會是一個靈性群體嗎?它看重和培養甚麼的靈性?這些靈性如何影響教會生活,並教會與社會的關係?教會如何藉其靈性轉化以情緒為主的文化政治?這些問題就留待給教會回應了。
(封面照片出自: MrT HK / CC BY;由九龍向北望的獅子山)
作者簡介/龔立人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香港基督徒學會義務總幹事。主要教授課程包括公共神學、基督教倫理、宗教與社會及生命教育。
認為教會是一個政治實體,其責任是向世界見證上主國的價值。所以,教會是一場參與轉化世界的政治運動。牧者是政治家,宣揚上主國、建立以教會為基礎的地方工作、培養信徒的心之習性。
傳揚論壇期待透過每篇文章激發更多基督徒思考信仰與社會的關係,不斷重新理解上主在這個世代的心意。 面對艱困的媒體環境與難以質疑、反省的教會文化,我們沒有教派包袱,願在各個公共議題上與大家一同反思。 為維持平台運作,傳揚論壇每個月需要15萬元經費,祈請兄姐關心代禱及奉獻,與我們同行,並向更多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