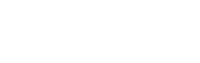近年来,社会越来越留意灵性(spirituality)与政治生活的关系。这是一件好事,因为灵性不再被视为只属于宗教、唯心和个人的事。然而,当下处理灵性与政治生活关系多倾向将灵性安放在个人身上,并从中探讨灵性对从政人和社会运动者的影响。
这类研究的不足之处,就是未能展现出灵性本身的政治向度。这篇短文尝试用亚美(Sarah Ahmed)提出的「情绪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概念思考灵性与政治生活的关系。
情绪的文化政治
简单来说,情绪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指情绪的社会性。它属于一种社会和文化实践多于一种个人心理状态,即情绪的文化政治是社会建构,并由此塑造我们对事物的解读,引导我们倾向它期望我们要有的某种反应和行为。
这些反应和行为是反射式(reactive),不是主动式;倚赖式,不是自主式。有别于论述,情绪的文化政治以挑动和强化我们最原始的情绪为主(例如,受威吓、憎恨、痛苦、厌恶和爱的情绪)。因情绪属于第一层次活动,它比理性对个人的影响更直接、更快,甚至更深刻。
情绪的文化政治多数由管治阶层借着某一事物或事件制造出来,透过不同媒体和活动,渗入个人生活,以致令人们产生相近的情绪。结果,管治阶层制造的情绪不但得以被提升和被放大,甚至成为维系社会要素之一。
在情绪的文化政治下,情绪是个人与社会之间沟通的媒体,而不是理性和理念。有别于感受(feeling),情绪的文化政治的核心不是个人对某一事物或事件的不同感觉,而是情绪的文化政治的目的是甚么、为谁服务、要达到甚么管治目的。
情绪的文化政治是任何一个政府或管治者常用的方法。例如,前南非白人政府在阿非利卡人(Afrikaners)中制造对黑人憎恨的情绪(黑人是次等,并威胁白人的安全)、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在美国人中制造对穆斯林恐惧的情绪(穆斯林是野蛮和暴力)、中国政府在中国人中制造以党国为核心的爱国情绪。
香港政府也不例外。1999年,香港政府以若不修改《基本法》对居港权的界定,于未来10年,将有167万人从中国到香港定居,香港将陆沉。香港政府制造受威胁的情绪,而最终,大部份香港人对修改《基本法》行动没有异议。
另一例子,自香港经历亚洲金融风暴和SARS,香港政府利用狮子山下的故事塑造一种面对逆境的文化政治,鼓励香港人。但实际上,政府借此要打造向北望文化(因为宣传片的狮子山是从九龙向北望)、不埋怨政府的忍耐和「肯挨」的态度。
然而,这十多年来,部份香港人对于政府带有政治目的制造出来的情绪文化政治越来越不为所动。例如,部份香港人对于以经济发展作为情绪的文化政治不为所动,反而以批判眼光看待高铁兴建、新界东北和大屿山发展、港珠澳大桥和自由行。在觉醒之余,我们是否也可能陷入韦伯(Max Weber)所说的,即从解魅进入另一著魅?
恐惧被动的文化政治
当政府管治越来越专横和野蛮,而一般的抗争行动没有带来实质转变时,有部份人对被动也恐惧起来。被动被视为是弱者的表现、容许被决定和被摆布,而最终被动使我们失去自己、坐以待毙。
在恐惧被动的文化政治下,抗争者刻意要反被动、反软弱、反被摆布,而行动就成为恐惧被动的文化政治之态度。以今年年初一和年初二凌晨警民冲突事件为例,掷砖头者认为这是官迫民反的结果,掷砖头是拒绝被动和表达自主的行动。
在《给港人的最后录音》,本土民主前线黄台仰说「宁为玉碎 不作瓦全」,以行动拒绝被动。专栏作家李怡说:「香港人必须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政治环境,升平时世已过去,抗争时代来临,不能再以旧日的太平心态去看待街头冲突。」
在恐惧被动的文化政治下,人若不愿做港猪(形容一些香港人不关心时事政治,崇尚玩乐和只顾自己,懒理不公义的事),就要站出来,用行动拒绝被动。然而,行动需要以不断升级克服对被动的恐惧。
虽然「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也是一种拒绝被动的行动,但在强烈恐惧被动的文化政治下,「和理非非」被批评为被动和左胶,因为他们仍在认同秩序的文化政治下生活。掷砖头是自主的表现,甚至拒绝为所做的负责任是公义的表现。
我承认不是一切抗争的行动都是源自恐惧被动的文化政治。那么,当下抗争行动是觉醒的结果还是受恐惧被动的文化政治主导?当下抗争行动是否唤醒睡着的人还是强化秩序和恐惧被动的文化政治?若情绪的文化政治特质之一是制造威胁的他者,当下抗争是否也制造威胁的他者,并将自己受害化?
灵性、情绪、理性
理性往往被视为对情绪有效的控制,但这种以理性控制情绪的思维犯了一个基本性毛病。即理性不是对立于情绪,理性更不必然优于情绪,因为理性也要回答那一种理性和谁人的理性。再者,理性可能是由情绪建构出来。
那么,在情与理外,政治生活需要灵性,作协调和整合。灵性是迈向他者,对比自身还要高的真善美之体验和向往,并从中产生促进万物间的公义和仁爱的价值、态度和生活实践。这使我想起一个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希特勒大军攻陷丹麦时,他强迫丹麦国王下一昭书,命令丹麦境内所有的犹太人戴上绣有达味(大卫)之星的黄臂章。丹麦国王知道希特勒的诡计是要将这些犹太人送往死亡集中营,然而他也知道违逆希特勒的后果将是多么地可怕,于是在下达昭书的同时,他先在自己的手臂上戴上了黄臂章,当所有的百姓看到国王的行动时,他们便知道了国王的用意,因此也都纷纷地戴上了黄臂章,于是乎,全国上下,不论是犹太人或是丹麦人,每一个人的手臂上都戴上了相同的黄臂章。这位丹麦国王为了拯救犹太人,冒普生命危险,戴上了黄臂章,而其人民也跟从了。
我曾跟丹麦朋友确认这事的真实性,但其回复是,历史没有这记录。然而,他写,「虽是如此,但若真有这事发生,我们丹麦人的回应会跟这故事一样。」(事实上,在拯救犹太人一事上,丹麦人民是佼佼者。)这故事表达出一份在情绪与理性以外的灵性,一份愿意为他者牺牲的精神。这份灵性不只是少数人拥有,更成为这国家的文化。
灵性是私人的,但不是个人(private, but not individual)。因此,灵性也是群体文化。事实上,没有群体文化向度的灵性,私人的灵性难以培育。那么,跟随的课题是:1.那些群体能培育灵性?2.他们培育甚么的灵性?3.这些灵性跟政治生活有甚么关系?4.他们如何跟一个情绪的文化政治对话?
教会是一个灵性群体吗?它看重和培养甚么的灵性?这些灵性如何影响教会生活,并教会与社会的关系?教会如何藉其灵性转化以情绪为主的文化政治?这些问题就留待给教会回应了。
(封面照片出自: MrT HK / CC BY;由九龙向北望的狮子山)
作者简介/龚立人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副教授、香港基督徒学会义务总干事。主要教授课程包括公共神学、基督教伦理、宗教与社会及生命教育。
认为教会是一个政治实体,其责任是向世界见证上主国的价值。所以,教会是一场参与转化世界的政治运动。牧者是政治家,宣扬上主国、建立以教会为基础的地方工作、培养信徒的心之习性。
传扬论坛期待透过每篇文章激发更多基督徒思考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不断重新理解上主在这个世代的心意。 面对艰困的媒体环境与难以质疑、反省的教会文化,我们没有教派包袱,愿在各个公共议题上与大家一同反思。 为维持平台运作,传扬论坛每个月需要15万元经费,祈请兄姐关心代祷及奉献,与我们同行,并向更多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