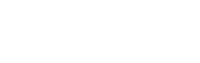我一直記得,在遙遠而模糊難辨的兒時回憶中,有一個奇特的夜晚。那是第一次,我的母親與我,在水和空氣都嚴重汙染的高雄家裡,盯著電視螢幕,看完了長達3小時的經典電影《十誡》。或許,那是我第一次熬夜?肯定的是,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美國人透過電影,想像以色列民族的解放故事。
到影片最後高潮時,在後有埃及追兵,前有大海阻隔的岸邊,面對因為害怕而提出倒戈歸順法老的以色列民,摩西的樣子簡直已經不像人了,他臉上沒有世人應有的軟弱,卻像個傻子一樣,轉身面向大海,張開雙臂說:「神將為我們爭戰,看啊!祂大能的臂膀!」
然後,紅海分開了。這或許是人類歷史上最有力的場景,激發了所有肩上與心頭擔著苦難的人至死不能放棄的盼望。
然而,真正讓我心裡一直無法忘懷的,是影片中的一個沒有名字的角色。在發現自己的猶太賤民的身世後,年輕的摩西隱姓埋名,側身於同胞之間,同擔苦役,在這一段過場中,摩西認識到過去身為王子時所無從體會的苦難。什麼樣的苦難呢?等待救贖致死的苦難。在和眾以色列人一同建立金字塔的時候,他伸手扶住了一個終生為奴、即將過世的老人,老人在死前卻對他說:「我的神遺棄我了,他沒有回應我的禱告,沒讓我在死前能見到我們的拯救者到來。」
他等到死,他沒等到,他不知道在他臨終前摟著他的,就是神即將重用的先知,因為摩西這時候也不知道自己將來要做的事。
在紅海邊,張開雙臂,與神同心,親眼看著神施展大能的那刻,摩西是否記得這個死在他懷裡的老人?
馬克思記得。據說,他在19世紀的英國,看過在工廠裡勞累至死的童工,這經驗讓他寫下「大工業是以希律王式的大規模掠奪兒童來慶賀自己的誕生的」這樣充滿悲憤的句子,基督徒當然看得出來,這短短一句話已經百轉千迴地藏著兩重控訴:希律王是為了除去耶穌而屠殺兒童,但馬克思為什麼要說這是「慶賀自己的誕生」?為什麼要把耶穌拖下水?這當然是因為體驗到神義論的破產過於疼痛!
在疼痛中,人自己站起來了。摩西的形象實在不像凡人,但耶穌的形象難道能抵擋暴力嗎?早在馬克思之前,盧梭在《社會契約論》裡就直接說了:「一個真正的基督徒的社會將不會再成其為一個人類的社會」,因為「只要不幸出現了任何一個野心家、任何一個偽善者」,那良善的基督徒又憑什麼不受奴役呢?「根本的問題乃是要上升天堂,而聽天由命只不過是上升天堂的另一種手段而已」。
因此,盧梭鼓吹要建立公民宗教,而在這公民宗教的基礎上,如今建立起了多少正義論的事業?哪一雙正義的眼睛,不是盯著紅海的另一端呢?
然而,現在卻得用人的血肉去分開紅海了,這過程不免血肉模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唱到:「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這長城又哪裡新了呢?不一樣是血肉嗎?人們不還是一樣和年輕時的摩西一起在金字塔下受苦致死嗎?
不一樣。摩西懷裡的老人,致死還在等待,盼望上帝回應他的禱告。但如今,禱告已然消失,盼望與等待都不復存在,只剩「起來」。
但真的可以沒有盼望嗎?
在20世紀,另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批判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西蒙‧韋伊,執意要改正這個錯誤。身為第一線勞工運動參與者、在法國小鎮高中教哲學、將工資分給勞工、組織工會後被開除並引以為傲的她,卻清楚地要求區分「不幸」與「不義」。奴役眾人來建立金字塔──或是長城──這是不義,人自然地反抗,要求改變現實,消除不義。然而,不能因為這樣,就說不幸一樣消除了。
死在摩西懷裡的老年奴隸,他在不義的體制底下受苦,但他一生中等待上帝回應的過程,感受到的卻是不幸。他的禱告確實包含著對消除不義的期待,但他求的卻不是看到不義的消除,而只是看到上帝還在乎,只要知道上帝有聆聽他的禱告,他就不再不幸了。不幸與不義相關,卻不相同。去除不義,還要擁抱不幸,不然,依然不是基督在乎每一個靈魂的摯愛。
而這樣的擁抱,要等待多久呢?摩西懷裡的老人,等到了人生的最後一刻。就算是一個無名的老人,神都在他睡了之前,回應了他。而今,在台灣等待著的每個人,不論是為了數十年前的大屠殺所留下的痛苦終能撫平,或是為了不再被當成錯誤創造而被剝奪平等權利的從過去到現在的每個世代,究竟還要等待多久呢?
而在各式各樣的不同族群的各種等待中,基督徒難道沒看到自己的影子嗎?基督徒,不正是從耶穌的時候起,就接續初代使徒,開始了持續至今的等待嗎?畢竟,只有基督徒懂得:等待(attente),就是盼望(attente)……
(封面《十誡》劇照來源:IMDB)
傳揚論壇期待透過每篇文章激發更多基督徒思考信仰與社會的關係,不斷重新理解上主在這個世代的心意。 面對艱困的媒體環境與難以質疑、反省的教會文化,我們沒有教派包袱,願在各個公共議題上與大家一同反思。 為維持平台運作,傳揚論壇每個月需要15萬元經費,祈請兄姐關心代禱及奉獻,與我們同行,並向更多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