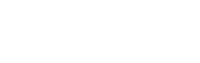謹以此文記念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難得的女牧者王貞文
不少人對500年前宗教改革的那段歷史與其神學的理解,存有二種迷思。一是認為,宗教改革是完全去性別的,與性別無涉。原因在於諸多對此時期進行的歷史研究只從男性中心的角色去作爬梳條理。長此以往,我們最常與宗教改革的聯想僅僅跟「五個惟獨」有關,即「惟獨信心」,「惟獨聖經」,「惟獨恩典」,「惟獨耶穌」,以及「惟獨上帝的榮耀」。而這「五個惟獨」看似普適於不同性別,自然孕育出性別盲的宗教改革記憶。
其二便是認定,由於新教對性採取較舊教更為正面肯定的態度,連帶地提昇了婦女當時的社會地位。畢竟馬丁路德主張婚姻內的性行為是神聖的,此舉大幅改善了恐性教會對女人的歧視與監控。但這樣的看法往往忽略了天主教內部為了因應宗教改革的衝擊,而出現的「反宗教改革運動」(anti-reformation movement),同樣推動某種體制內的變革。因而,與其說這樣的認定是貼進歷史事實的評價,倒不如說,更多反應了新教形塑自身「改革者」形象的不遺餘力。
所幸,隨著性別研究的崛起,促使近來不少教會歷史學者開始追問,改革宗信仰與天主教在這個時期的諸多改革對婦女所帶來的衝擊和影響究竟為何。
宗教改革的女性身影
一般來說,有性別意識的歷史學者對宗教改革這時期的研究旨趣,主要集中在二個面向上,首先,婦女亦是宗教改革的參與者,到底她們那個時候扮演的角色為何?其次,以男性改教者為主導的宗教改革與反改革運動,究竟透過哪些措施在「改革」或「宰制」婦女的言行舉止?
對於前者,越來越多過去不被重視的婦女史料,受到重新檢視,焦點多放在那些有著堅定獨立意識的婦女,像是違逆丈夫意志改宗的妻子,抑或是接受新教但卻仍舊留在天主教的修道院中的修女,還有那些因著家庭階級或特殊教會背景的優勢,得以站上宗教改革運動的風頭浪尖上,成為代表性女性領袖,諸如: Argula von Grumbach、Marie Dentiere、Angela Merici,以及Teresa Avila。好奇的是,她們究竟採取了哪些奏效的策略,為自己掙出一片天?
這個向度的婦女歷史研究,想要呈現出的,不單單是一個受害者的面貌,更是反抗者的肖像。哪裡有壓迫,哪裡便有反抗。如同Merry Wiesner 所指出的,當宗教改革時期,不論新、舊教,視女性為性的受造,嘗試控管或規訓她們的性,許多婦女卻不因著生理性別而自限,大膽地依靠自己從上帝所領受的屬靈恩賜,以及智性的出眾,獲得了某種程度的自主。
至於後一個問題,宗教改革時期社會對「第二性」的控制,手法其實百百種。其中最為首要的,是透過對社群意識的營造,將她們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研究宗教改革時期德國婦女如何適應新教「社群」(community)的學者Lyndal Roper以為,很可惜,那時的新教「社群」根本上仍是父權的,婦女往往無法參與擔任公職者公開起誓的這類具公共意涵的社會儀式,顯示這樣的「社群」並未把婦女亦視為是公共領域的一份子。理所當然,當婦女試圖發動自己的政治訴求時,他們零星的反抗行動往往被視為是違逆了社會有關於性別的規範,是具顛覆性的,恰如同當時的農民革命一般,應當嚴加控管。
Gabriella Zarri則把焦點放在天主教女性聖徒的宗教經驗上,她指出一項不容忽略的事實,15世紀天主教內部女修會數量顯著增加。特別是由平信徒婦女所組成的「第三修會」(the Third Orders),她們認同在修會需遵守的規範,彼此相伴生活在一處,但卻沒有發聖願。無奈,隨著旨在反新教改教運動的特倫托會議(the Council of Trent)召開,教廷開始緊縮這類「第三修會」的存在空間,修道院愈發與外隔絕,「第三修會」的成員被要求轉為修女,並且住在修道院中。順此,從15世紀中葉到17世紀,女性遭冊封為聖徒的總人數開始下降,而少數封聖的婦女,形象也從過去佔多數的秘契主義者,轉而成為修道院的改革者。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這些聖女,社會上還有不少「墮落」(fallen)的婦女,像是被控從事非法性行為的,如娼妓、失去家庭支持的婦女等。Sherrill Coheng在探討天主教的反改革運動與婦女避難所的關係時,發現在這個時期,有非常多的新型態的、類似現今所謂的「中途之家」成立。
錯綜複雜的女性地位
大約從16世紀起,就有不少是專門收容「墮落」婦女的這類「中介」機構,一方面,這裡的生活具有懲戒的性質,但婦女在這裡停留的時間,亦具備某種「過渡儀式」(rite of passage),藉以獲得「淨化」,以便日後可以重拾尊嚴復歸社會。同其時,亦有不少機構是提供在天主教會下無法離婚,但卻亟需要逃離施虐丈夫及遭遺棄的不幸婚姻的婦女的,免得她們進一步受到性的誘惑而沈淪。
同其時,隨著方方面面的宗教改革時期婦女歷史研究問世,環繞著家庭的新舊教相關爭議,也浮上了檯面。傾向支持舊教的學者主張,新教的改教運動,強調以成家來取代守獨身作為更好的在世生活的選擇,配合強迫關閉修道院的種種措施,乍看之下,彷彿是對性壓抑的翻轉、道德鬆綁,事實上,卻有害於婦女脫離父權家庭的宰制,讓她們再無「破門出家」的可能,而不得不更加地臣服於父兄及丈夫。
但持不同看法的學者,如Steve Ozment卻主張,縱使新教根據聖經所言「丈夫是妻子的頭」,支持男性家長制,但新教對婚姻的理解基本上是男女平等的夥伴關係,並且容許離婚與再婚,這些作法使得婦女得以解放,不必再忍受不人道的婚家鉗制。
離婚制度的成立的確是創舉,但Jeffrey Watt實際檢視當時離婚成立的要件及實施的情況,便發現離婚仍舊只是少數,而且侷限在通姦和遺棄二類情況,至於對待妻子殘酷的理由,從16世紀一直到17世紀,都不被教會接納。歐洲的家事法庭對那些遭到丈夫虐求的妻子並沒有提供多大幫助。對待通姦的性別雙重道德標準,仍舊非常普遍,法庭不僅常拒絕遭誘姦的女性提出的婚姻訴訟案,而男性因此得到的刑罰,相較於女性,亦往往輕得多。
由此可知,宗教改革運動在當時所打開的性別解放之門,並沒有想像的大,且若無其他諸如就業及社會安置機轉作為配套,其實充其量是看得見吃不到的畫餅罷了。
整體而言,宗教改革對婦女的衝擊,很難簡單以進步或退步來概括。比如說,縱使在修會中的女性地位,往往因新教的宗教改革,而面臨倒退,但在新教主導的地區,一般婦女的教育機會卻大大增加。至於那些,沒有政治影響力及經濟機會的、絕大多婦女,改教前與改教後,不論是在路德宗、加爾文、安立甘或是天主教的領土上,處境其實沒有多大的改變。不過,上述的性別歷史研究均指出,不同的社會位置、地區的文化差異,和家庭的階級背景,對個別女性的自我發展空間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為什麼一個號稱改革的時代,在性別平等的意識上,卻缺乏夠革新的覺醒?當新教宣稱改革是一個不斷進行的運動,不夠改革的過去,到底對日後的教會傳統、神學建構帶來什麼持續影響?更重要的是,當新教傳入多元文化和族群的台灣,究竟哪些性/別議題的發燒引發基督教會與社會嚴重對立,本土婦女神學又該如何汲取過去宗教改革運動的歷史教訓,透過除了聖經及教會傳統之外的其他二大神學支柱——理性與經驗,在現階段教會內革新與守舊的張力中,掙扎前行?
這是現階段號稱「釘根在本土,透過愛與受苦,成為盼望的記號」的基督教會在紀念宗教改革500週年時,所不得不思索的課題。
(封面相片來源:Gustavo Minas / CC BY-NC)
傳揚論壇期待透過每篇文章激發更多基督徒思考信仰與社會的關係,不斷重新理解上主在這個世代的心意。 面對艱困的媒體環境與難以質疑、反省的教會文化,我們沒有教派包袱,願在各個公共議題上與大家一同反思。 為維持平台運作,傳揚論壇每個月需要15萬元經費,祈請兄姐關心代禱及奉獻,與我們同行,並向更多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