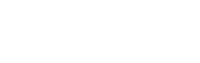谨以此文记念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难得的女牧者王贞文
不少人对500年前宗教改革的那段历史与其神学的理解,存有二种迷思。一是认为,宗教改革是完全去性别的,与性别无涉。原因在于诸多对此时期进行的历史研究只从男性中心的角色去作爬梳条理。长此以往,我们最常与宗教改革的联想仅仅跟「五个惟独」有关,即「惟独信心」,「惟独圣经」,「惟独恩典」,「惟独耶稣」,以及「惟独上帝的荣耀」。而这「五个惟独」看似普适于不同性别,自然孕育出性别盲的宗教改革记忆。
其二便是认定,由于新教对性采取较旧教更为正面肯定的态度,连带地提升了妇女当时的社会地位。毕竟马丁路德主张婚姻内的性行为是神圣的,此举大幅改善了恐性教会对女人的歧视与监控。但这样的看法往往忽略了天主教内部为了因应宗教改革的冲击,而出现的「反宗教改革运动」(anti-reformation movement),同样推动某种体制内的变革。因而,与其说这样的认定是贴进历史事实的评价,倒不如说,更多反应了新教形塑自身「改革者」形象的不遗余力。
所幸,随着性别研究的崛起,促使近来不少教会历史学者开始追问,改革宗信仰与天主教在这个时期的诸多改革对妇女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究竟为何。
宗教改革的女性身影
一般来说,有性别意识的历史学者对宗教改革这时期的研究旨趣,主要集中在二个面向上,首先,妇女亦是宗教改革的参与者,到底她们那个时候扮演的角色为何?其次,以男性改教者为主导的宗教改革与反改革运动,究竟透过哪些措施在「改革」或「宰制」妇女的言行举止?
对于前者,越来越多过去不被重视的妇女史料,受到重新检视,焦点多放在那些有着坚定独立意识的妇女,像是违逆丈夫意志改宗的妻子,抑或是接受新教但却仍旧留在天主教的修道院中的修女,还有那些因着家庭阶级或特殊教会背景的优势,得以站上宗教改革运动的风头浪尖上,成为代表性女性领袖,诸如: Argula von Grumbach、Marie Dentiere、Angela Merici,以及Teresa Avila。好奇的是,她们究竟采取了哪些奏效的策略,为自己挣出一片天?
这个向度的妇女历史研究,想要呈现出的,不单单是一个受害者的面貌,更是反抗者的肖像。哪里有压迫,哪里便有反抗。如同Merry Wiesner 所指出的,当宗教改革时期,不论新、旧教,视女性为性的受造,尝试控管或规训她们的性,许多妇女却不因着生理性别而自限,大胆地依靠自己从上帝所领受的属灵恩赐,以及智性的出众,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主。
至于后一个问题,宗教改革时期社会对「第二性」的控制,手法其实百百种。其中最为首要的,是透过对社群意识的营造,将她们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研究宗教改革时期德国妇女如何适应新教「社群」(community)的学者Lyndal Roper以为,很可惜,那时的新教「社群」根本上仍是父权的,妇女往往无法参与担任公职者公开起誓的这类具公共意涵的社会仪式,显示这样的「社群」并未把妇女亦视为是公共领域的一份子。理所当然,当妇女试图发动自己的政治诉求时,他们零星的反抗行动往往被视为是违逆了社会有关于性别的规范,是具颠覆性的,恰如同当时的农民革命一般,应当严加控管。
Gabriella Zarri则把焦点放在天主教女性圣徒的宗教经验上,她指出一项不容忽略的事实,15世纪天主教内部女修会数量显著增加。特别是由平信徒妇女所组成的「第三修会」(the Third Orders),她们认同在修会需遵守的规范,彼此相伴生活在一处,但却没有发圣愿。无奈,随着旨在反新教改教运动的特伦托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召开,教廷开始紧缩这类「第三修会」的存在空间,修道院愈发与外隔绝,「第三修会」的成员被要求转为修女,并且住在修道院中。顺此,从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女性遭册封为圣徒的总人数开始下降,而少数封圣的妇女,形象也从过去占多数的秘契主义者,转而成为修道院的改革者。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这些圣女,社会上还有不少「堕落」(fallen)的妇女,像是被控从事非法性行为的,如娼妓、失去家庭支持的妇女等。Sherrill Coheng在探讨天主教的反改革运动与妇女避难所的关系时,发现在这个时期,有非常多的新型态的、类似现今所谓的「中途之家」成立。
错综复杂的女性地位
大约从16世纪起,就有不少是专门收容「堕落」妇女的这类「中介」机构,一方面,这里的生活具有惩戒的性质,但妇女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亦具备某种「过渡仪式」(rite of passage),藉以获得「净化」,以便日后可以重拾尊严复归社会。同其时,亦有不少机构是提供在天主教会下无法离婚,但却亟需要逃离施虐丈夫及遭遗弃的不幸婚姻的妇女的,免得她们进一步受到性的诱惑而沈沦。
同其时,随着方方面面的宗教改革时期妇女历史研究问世,环绕着家庭的新旧教相关争议,也浮上了台面。倾向支持旧教的学者主张,新教的改教运动,强调以成家来取代守独身作为更好的在世生活的选择,配合强迫关闭修道院的种种措施,乍看之下,仿佛是对性压抑的翻转、道德松绑,事实上,却有害于妇女脱离父权家庭的宰制,让她们再无「破门出家」的可能,而不得不更加地臣服于父兄及丈夫。
但持不同看法的学者,如Steve Ozment却主张,纵使新教根据圣经所言「丈夫是妻子的头」,支持男性家长制,但新教对婚姻的理解基本上是男女平等的伙伴关系,并且容许离婚与再婚,这些作法使得妇女得以解放,不必再忍受不人道的婚家钳制。
离婚制度的成立的确是创举,但Jeffrey Watt实际检视当时离婚成立的要件及实施的情况,便发现离婚仍旧只是少数,而且侷限在通奸和遗弃二类情况,至于对待妻子残酷的理由,从16世纪一直到17世纪,都不被教会接纳。欧洲的家事法庭对那些遭到丈夫虐求的妻子并没有提供多大帮助。对待通奸的性别双重道德标准,仍旧非常普遍,法庭不仅常拒绝遭诱奸的女性提出的婚姻诉讼案,而男性因此得到的刑罚,相较于女性,亦往往轻得多。
由此可知,宗教改革运动在当时所打开的性别解放之门,并没有想像的大,且若无其他诸如就业及社会安置机转作为配套,其实充其量是看得见吃不到的画饼罢了。
整体而言,宗教改革对妇女的冲击,很难简单以进步或退步来概括。比如说,纵使在修会中的女性地位,往往因新教的宗教改革,而面临倒退,但在新教主导的地区,一般妇女的教育机会却大大增加。至于那些,没有政治影响力及经济机会的、绝大多妇女,改教前与改教后,不论是在路德宗、加尔文、安立甘或是天主教的领土上,处境其实没有多大的改变。不过,上述的性别历史研究均指出,不同的社会位置、地区的文化差异,和家庭的阶级背景,对个别女性的自我发展空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为什么一个号称改革的时代,在性别平等的意识上,却缺乏够革新的觉醒?当新教宣称改革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运动,不够改革的过去,到底对日后的教会传统、神学建构带来什么持续影响?更重要的是,当新教传入多元文化和族群的台湾,究竟哪些性/别议题的发烧引发基督教会与社会严重对立,本土妇女神学又该如何汲取过去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教训,透过除了圣经及教会传统之外的其他二大神学支柱——理性与经验,在现阶段教会内革新与守旧的张力中,挣扎前行?
这是现阶段号称「钉根在本土,透过爱与受苦,成为盼望的记号」的基督教会在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时,所不得不思索的课题。
(封面相片来源:Gustavo Minas / CC BY-NC)
传扬论坛期待透过每篇文章激发更多基督徒思考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不断重新理解上主在这个世代的心意。 面对艰困的媒体环境与难以质疑、反省的教会文化,我们没有教派包袱,愿在各个公共议题上与大家一同反思。 为维持平台运作,传扬论坛每个月需要15万元经费,祈请兄姐关心代祷及奉献,与我们同行,并向更多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