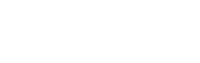一、
16世紀的歐洲並沒有出現現代的「國家」(State),他們是活在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的管治底下。從中世紀早期開始,一直到1806年解體為止,神聖羅馬帝國的版圖主要是歐洲中部,其地域是多種族的而非單一種族的,不同種族共同活在神聖羅馬帝國的管治底下。因此我們的題目稱為「路德與德意志民族主義」,探討路德在宗教改革時期與德意志民族主義的關係。
二、
德意志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或民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是甚麼時候出現、興起的?路德在其中又扮演了甚麼角色?第二次大戰之後,不同學科的學者都嘗試解釋為甚麼德國民族主義會出現極端發展的情況,有些追溯至路德的宗教改革所涵蘊的德意志民族主義。1976年基斯特納(W. Kistner)發表文章:〈宗教改革與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根源〉(The Reformation and the Roots of German Nationalism)(刊於Theoria:A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46 (May 1976): 61-76),得出下面五點結論:
- 在路德因為攻擊「贖罪券」(indulgences)的賣買而聲名大噪之前,在德意志的知識與貴族之中,德意志的民族意識就已經堅穩地建立起來了。
- 16世紀初的德意志民族意識早已預告20世紀德意志民族主義好些特徵。未能建立政治上的一統,這種挫敗在浮現中的民族是一股強大的推力,有助推動民族主義。
- 在路德的宗教改革的浪潮之中、在借鑑路德向德意志社會所有階層發表的著作之下,德意志人文主義者對德意志民族的看法越過了德意志社會的階層障礙。
- 環繞在路德四周的宗教改革,跟德意志的人文主義無疑互有關連,但在根源上和看法上十分不同,他們是兩種不同的運動。
- 德意志的路德宗教改革,除了堅持唯獨倚靠上帝的話語,也尋求地方諸侯的支持。這就引致削弱眾教會對政治的、社會的和經濟的難題的見證了。(頁69-70)
在這裡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無疑,路德所發起的宗教改革跟德意志人文主義推動的民族主義是兩種不同的運動,但這並不表示路德不同意、不支持、不借用民族意識來推動宗教改革運動。這涉及了路德是怎樣看待(在信仰上在行動上)民族主義、民族意識的。這一問題,是否涉及第五點所講的?基斯特納沒有在路德借助德意志地方諸侯的力量進行宗教改革作出任何探討,甚為可惜。因為極有可能的是,路德是訴諸德意志民族主義,來獲取德意志地方諸侯支持宗教運動,以抗衡羅馬天主教會的制肘甚至迫害。
三、
2015年梅辛格(Dean Messinger)寫成〈路德宗教改革中的民族主義於民族建立〉(Nationalism and Nation-building in the Lutheran Reformention),在其引言中指出:
藉著擁護「德意志民族的困苦/苦境」(Gravamina nations Germanicae, the grievances of German nation)因由,以致使得德意志身份成為他論辯中的核心部分,路德得以獲取政治的支持推動他的運動,以致把新教的眾多德意志地方政權建立成核心的和主權的地位。首先是普魯斯公國(the Duchy Prussia),這是宗教改革的產物,也揭示了世界的權力正在成形。(頁1)
在其結論中這樣寫道:
普魯斯的例子建立了德意志身份與路德主義(Lutheransim)互相交織的先例,在其中路德為了德意志有意義的改革而決定了最佳的行動路線,就是強調政治統治者在改革中扮演催化劑的角色。在普魯斯的個案之中,失去條頓秩序(Teutonic Order)的德意志身份這種恐懼,被使用來推動宗教改革朝向政治目的來發展,而路德則使用火熱的民族主義的和政治的修辭,遊說德意志貴族教會改革的需要。路德重新定義諸侯的權力:同時在俗世的和宗教的事務上擁有權力,這就播下了種子,讓17世紀的絕對統治和君主主權的概念得以出現。使用民族身份作為宗教改革的工具,成為了繼後所有改革的共同手法,並激起了獨特有別的「民族的/國家的」信義宗教會在整個歐洲出現。(頁21)
那麼,為甚麼會出現這種狀況?為甚麼路德可以成功地獲取德意志諸侯及貴族的支持,幫助他推動宗教改革?梅辛格經過分析之後指出了兩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德意志民族的困苦/苦境」使得德意志貴族與羅馬公教教皇之間出現了磨擦與不信任,另一是:羅馬教會和神聖羅馬帝國都缺乏能力解決這困難局面,這就造就了條件有利宗教改革得以發展,那些感到被教皇「濫用」的人,愈來愈想棄絕羅馬公教。(頁8)他們很快發現路德是他們最有效的發言人。(頁8)
1455年的「德意志民族的困苦/苦境」,是回應1448年教皇尼古拉斯五世(Pope Nicholas V)與皇帝弗雷德里克三世(Emperor Fredeside )簽訂的維也納協約(Vienna Concordat)。這協約成為德意志貴族與羅馬公教教會磨擦的主要根源,因為它重建教皇在德意志之中可以行使的權力,包括推動宗教選舉與收稅的權力(許可教皇收取德意志教士俸祿的首年捐,即每一教士俸祿第一年的一半)(頁2)。維也納協約也導致並增加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與德意志貴族之間的不信任,德意志貴族視維也納協約的簽訂是「出賣民族利益,或至少未能保護他們的利益」。大多時候,德意志貴族與皇帝的衝突在於皇帝有權徵稅和建立帝國的軍隊。(頁3、4)
在「德意志民族的困苦/苦境」之中最為獨特的控訴是涉及德意志獨特有別的身份。「德意志民族的困苦/苦境」有著傾向獨立思考的味道,看來好像是初步的德意志民族主義的發端,路德馬上抓住這事實並使之成為改革的核心部份。「德意志民族的困苦/苦境」的其中一個關鍵是挑戰「無情地強加教皇的徵稅」、「法蘭西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掌管教廷,德意志的土地被用來餵養那些教皇和他們爪牙頹廢的生活」,德意志人也抗議教皇和教廷「委任外國人在德意志隨意出任教會職位」。(頁5)
另一個引致德意志民族主義起來挑戰教皇權柄的是關乎替查理曼(Charlemagne)加冕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他們認為「上帝已經把羅馬帝國賜給德意志人」,所以質疑教皇是否有權同時統治俗世的與屬靈的領域。這觸動了許多德意志內的俗世領袖,許多地方的統治者都對教皇宣稱擁有俗世權力感到憤怒,他們不滿意別人插手干預德意志內部的事務。這種觸動使得德意志強大的俗世力量都支持路德和他的改革。(頁6)
此外,這個時間的印刷術有突破性的發展,人文主義的學者藉此而發表許多文章,建構德意志人的民族自我形象。在宗教改革之前已出現了有關德意志身份的關注與討論,德意志人開始欣賞自己的過去,而有別於羅馬人。這指向了在宗教改革之前已經出現了「德意志民族統一體」的看法,由許多共通的習俗與一個共同的歷史所表達。(頁6-7)
還有最為深刻的是 ,在德意志族群對神聖羅馬帝國的掙扎,與德意志改革者對羅馬公教教皇的掙扎這兩者之間的平行。前者的特徵是「德意志的自由……對抗南部貪婪的意大利人」,後來宗教改革以此為寓言影射羅馬公教教會。(頁7)路德底下的學者和作家,把新教徒等同真正的德意志人,等同上帝的選民。他們相信「正如神聖的拯救在以色列民的歷史之中顯現,現在也一樣」,上帝會因著他們的緣故而介入。(頁7-8)
從以上所講的,大概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當時德意志的貴族與路德為什麼會走在一起。簡單來說,當政治改革有利於宗教改革,宗教改革有利於政治改革,兩者就會互相支持,彼此聯合起來。我們不能否定在這個過程之中,路德借用了德意志民族意識,使德意志貴族支持宗教改革,從羅馬公教教會脫離出來。
四、
路德這種舉動,我們可以在他的著作之中找到印證,特別是他在1520年出版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公開書》(The Christian Nobility of the German Nation concerning the Reform of the Christian Estate)。路德在這著作之中以信徒皆祭司為武器,拆毀由教皇制度所建立的三層城牆:屬靈高於俗世權、教皇有解釋聖經全權、教皇有召開教會會議全權。
無疑,路德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公開書》其中一個主要關注是把教會去中心化,努力減少羅馬教會的中心權力,使得德意志的教會減少各種負擔特別是經濟上的負擔,而變得更加獨立自主(頁11)。但是他在這本著作之中把羅馬公教教會和教皇,不單跟德意志教會連上關係,更跟德意志民族的前途連上關係。因此有學者就認為這著作反映了「德意志民族的困苦/苦境」背後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路德看到這新興的民族主義者的觀點,跟聖職改革的需要十分吻合配對,而可以使用民族的身份作為背境,清楚訴諸民族的權力與德意志人的驕傲來煽動俗世的統治者。(頁11)
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公開書》之中,路德戲劇性地揭示德意志會被羅馬公教教會毀滅。路德這樣寫道:「我們現在看到義大利成了荒野——修道院傾圯了,主教區被吞噬,所有教區和教會的收入都被羅馬吸乾,城市衰落,土地荒涼,人民稀少,因為一切禮拜和講道都沒有了——為甚麼呢?因為那些主教要有收入。」(《路德選集》上冊,2017,頁199)路德預見如果德意志繼續活在教皇這種不道德的管制底下,這就是結果。他繼續寫道:「現在義大利被搜刮一空,他們來到德意志,開始是如此溫和!但我們要小心,否則德意志不久就如義大利一般。」(《路德選集》上冊,2017,頁199)路德把教皇和樞機主教描繪成德意志的敵人,不單有目的地殘害德意志的敬虔,更會毀滅德意志,這就起著作用,把宗教改革、反抗教皇權威,鑄造成所有德意志人的愛國責任、義務。(頁11-12)
事實上,路德花了大量篇幅揭露教皇和教廷的財政濫用,特別收取德意志貴族不合比例的重稅。他寫道:「我相信德意志現在所付給教皇的,比以前付給眾皇帝的還要多。〔……〕(《路德選集》上冊,2017年,頁200)「〔他們〕以為瘋狂的德意志人永遠至愚,將無止境地供給他們金錢,滿足他們無窮的貪慾。」(《路德選集》上冊,2017年,頁201)在「德意志民族的困苦/苦境」中,第一點講的就是教皇和教廷對德意志的經濟剝削,使得德意志貴族怨聲載道。
因此,有學者就說路德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公開書》花了大部份篇幅討論俗世事務,展示了德意志需要在社會和經濟上的連串改革,這就顯出路德認同「德意志民族的困苦/苦境」,更提供了一個他們之前沒有想過的神學基礎,讓他們改革有理。(頁9)
如前所說,路德使用「信徒皆祭司」為武器攻擊教皇,既限制他的權柄,又高抬俗世的權柄。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公開書》他就有下面的說話:
德意志民族、主教和諸侯應該想到自己也都是基督徒,應該在世俗的和宗教的事務方面保障人民,反對這些披著羊皮裝作牧人與統治者的豺狼。(《路德選集》上冊,2017,頁201-202)
執政者既是和我們一樣,受同樣的洗禮,而有同樣的信心和福音,我們必須承認他們是祭司和主角,並以他們的職務在基督徒社群中,有著適當和有用的地位。(《路德選集》上冊,2017,189。)
由此可見,在一般信徒和神父、貴族和主教,以及「屬靈的」和「屬世的」之間,實在沒有甚麼差別,他們的所謂差別,不過是職務和工作上的差別,而不是「階級」上的差別;因為他們都是屬同一階級,都是真的祭司、主教和教宗,不過他們正如神父和修士工作不同一樣,並不都是擔任同樣的工作而已。(《路德選集》上冊,2017,頁190)
〔……〕同樣俗世掌權者也一樣,他們不過受了委託,拿著刀和杖來懲罰惡人,保護善人。(《路德選集》上冊,2017,頁190)
俗世的權力既然是上帝所派來懲罰惡人、保護善人的,所以應在整體基督教界中自由地行使它的職務,無論對教宗、主教、神父、修士、修女或任何人,都不徇情面。(《路德選集》上冊,2017,頁191)
因此基督徒俗世權力應該無阻地行使它的職務,不管是否涉及教宗、主教或神父;誰犯了罪,誰就應受處分。(《路德選集》上冊,2017,頁191)
因此基督教的貴族應該起來反對教宗,如同基督教的公敵和毀滅者一般。他們為拯救那些因教宗的專制而勢必趨於毀滅的可憐人,就應該這麼辦。」(《路德選集》上冊,2017,頁211)
花上這麼長的篇幅引述路德的說話,不過是要表明他的確就如學者的分析,的確要求「基督徒的權柄(如諸侯、公爵等)質詢聖職及層級,它們不再履行其職責,因此必須把改革教會的事情放在自己的手裡」,而宣告德意志貴族必須領導改革的運動,教皇已經不能履行其基督徒的責任了。(頁9)
但是學者提出了問題,認為路德如此一來就為教會帶來困難,甚至危險。因為把宗教力量置於俗世統治者手裡,會使得德意志諸侯戲劇性地擴展及集中其勢力。以為「統治的諸侯擁有權柄及基督徒責任去管治教會」,只會給予野心的諸侯有機會實現十五世紀的野心:俗世權柄高於教會權柄。(頁9-10)後來新教的統治者就使用路德的神學來正當化合法化自己的行動:挪用教會的財產與掠奪教會的財富來償還自己的私人欠債與增強帝國的力量。(頁10)
路德也支持最高主教(summus episcopus)的意念,並且統治的諸侯可以擔任最高的聖職,這就創造了一種國家教會了,俗世的領袖以「緊急主教」(emergency bishop)來在教會的領域之中行使其權力。路德把教皇與皇帝的權力與責任,置於德意志主權統治者的手裡。(頁10)
來到這裡,我們發現路德最後引致國家教會的出現,而更為重要的是容讓統治者介入教會的管治之中。路德因為要讓德意志的教會從羅馬公教教皇脫離出來,借用了德意志的民族主義或民族意識來鼓勵甚至鼓動德意志眾多地方諸侯,結果反過來引入了俗世權力參與教會的管治,使得後來德意志的教會不得不依附地方統治者,削弱了他們在政治上、社會上與經濟上各方面的見證。這樣的結果,可以在20世紀30年代德國教會的遭遇上清楚看見。
(封面相片來源:Anton von Werner, 1877;馬丁路德在沃木斯議會上面對皇帝查理五世與教皇利奧十世。)
作者簡介/鄧紹光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基督教思想(神學與文化)教授
傳揚論壇期待透過每篇文章激發更多基督徒思考信仰與社會的關係,不斷重新理解上主在這個世代的心意。 面對艱困的媒體環境與難以質疑、反省的教會文化,我們沒有教派包袱,願在各個公共議題上與大家一同反思。 為維持平台運作,傳揚論壇每個月需要15萬元經費,祈請兄姐關心代禱及奉獻,與我們同行,並向更多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