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转型(期)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在台湾所要处理的议题集中在二个时期政府对于人权的侵害上,一是二二八屠杀事件,另一则是白色恐怖。目标则是诉诸对受害者及其家庭的肯认与补偿,调查历史真相,检讨与反省加害者及加害体系。
在签署二公约后,台湾在2012年进行了第一次国家报告的审查,在〈结论性意见与建议〉第24点亦这样说,「解严之前的压迫与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事件对中华民国(台湾)社会留下巨大伤痕。政府为了抚平历史伤口及赔偿受害者而采取了某些措施,包括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以及建造二二八事件纪念碑。然而,转型时期尚未结束,需要政府更多作为来促成中华民国(台湾)社会的和解。赔偿权应包括被害人在社会与心理层面的复原,也应同时赋予追求真相与正义的权利。」
转型(期)正义,涉及二个要求,一是正义,另一是转型。可惜一直以来,台湾社会因着蓝绿对立,争议的多半是转型(期)正义「不正义」的部份,却很少有人费功夫着墨转型(期)正义「不转型」的可能。正是基于转型(期)正义的推动有可能既不正义又不转型,不少国外学者开始要求另一种转型正义(transformative justice),认为即便转型(期)正义不能完全由转型正义所取代,转型(期)正义的理念与作法都必须更朝向转型正义来发展。
转型(期)正义有个很清楚的运用脉胳,是「政权变迁后,新政府处前朝政府所遗留下的历史问题的方式,目的的可能是清算旧政府之不义,或是补偿旧政府时期的政治受害者」(Elster 2004)。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学者Ruti G. Teitel在《变迁中的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中,提到这样的一个正义的概念不仅限于传统法律的框架,涵盖的范围可以涉及如刑事正义、历史正义、补偿正义、 政治正义,以及宪法正义等等(Teitel 2000)。
联合国相关文献更直陈转型(期)正义的种种措施必须紧扣着人权及法治来设置,「要协助因冲突所破坏的社会,或协助脱离压迫政体的社会,重建法治并处理大规模的人权违犯,特别是在一个体制崩毁、资源秏尽、社会安全低落、人们受挫且分歧的处境中,这是艰巨的挑战。……经验显示,要提倡复合及巩固和平,长期而言,需要建立或重建能有效治理的行政及司法体系,而这些必须建基在尊重法治及人权保障上。」。而转型(期)正义经常使用的措施包括有: 司法审判,诉说真相,体制改革,以及补偿程序等等。
一开始,转型(期)正义并不打算也不能够成为处理所有不正义议题的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台湾社会曾经就「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是否纳入原住民议题,有过激烈的争议。支持分开处理者,诉诸的理由是,联合国《消除一切种族歧视公约》及《原住民族权利宣言》所论及的回复原住民族历史正义,要求的是,侵略与殖民真相之调查与公开,文化保全与安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平权,以及法主体之建立等,这些都和转型(期)正义的核心意义并不相同。反对分开处理者,却以未纳入原住民族作为指控政府的「促转条例」是选择性正义,难免有政党恶斗及挟怨抱复的嫌疑,担忧在非黑即白的二元仇恨对立中,原住民的相关权益会被牺牲掉。
然而,随着对转型(期)正义的修正,转型(期)正义也逐渐被视为是可以用来处理并未出现转型期的社会其内部冲突的机制。有学者便进一步依据转型(期)正义的系谱学研究,将转型(期)正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且以冷战时代的出现告终,这期间转型(期)正义被看作是例外的、跨国性的措施。第二个时期是1989年以后后冷战时期,随着不少国家民主化及现代化的出现,转型(期)正义是连同不同的社会处境及法律来进行论述的。第三个时期则是在二十世纪末出现,针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政治不稳定及暴力的正常化现象,来谈转型(期)正义,亦是所谓的「稳定时期的转型(期)正义」(steady phase of transitional justice)。于是转型(期)正义不再被视为是一种例外,抑或是某种过渡阶段的作法,而是一种常态,最明显的例证便是伴随着国际人道法的崛起而成为联合国常设组织的「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的出现(Teitel 2003)。在这个意义下,「转型(期)正义」意味着的仅仅是,带有某种工具性的价值,其目的在促成某种政治上转变的,针对特殊的、一定时间范围内的某种形式的正义。
转型中的转型(期)正义
截至目前为止,转型(期)正义在世界各地的实施,一般来说,成效和影响都不明确,甚至是令人失望的,受批评的,或被讥为「成功者的正义」,或是认为顶多能「治标而无法治本」。
学者Paul Gready and Simon Robins在〈From Tansitional To Transformative Justice: A New Agenda for Practice〉一文中便批评转型(期)定义受到二种类型的限制,一是基本的,另一是次级的。基本的限制指的是自由主义式的和平理念,以及由上而下的以政府为主的进路。至于次级的限制,则主要是由基本限制所导出的「离地的」实施措施,以致于未能促进社会真正的转变。
自由主义的和平理念主要是受到二种全球化的影响而形塑的,一是自由主义有关于公民及政治权利的典范,因而强调选举、程序民主,立宪主义,法律的治理,以及诸多向后回顾的确之真相与正义的措施。另一则是则是由市场所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以及所谓「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干预措施。
上述的作法,偏好在脆弱的转型期处境中,优先创设一些机构,而不是用更具脉络的方式来促进大众的福祉,这招致了不少批评。到底何谓「脆弱的转型期处境」?根据2011年的「新方案」(New Deal) 是这样界定的,「缺乏能力或意愿去逐步促进公民共同的发展,并且特别容易因外在的动荡及内部的冲突而受挫。」虽然有了新机构,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最终在运作上被架空,而无能积极回应公民社会的真正需求。因此,在处理过往的不正义时,转型(期)正义过于关注加害者个人或政府的暴力,却无法处理结构性的暴力及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由上而下的国家主导进路则往往侷限在跨国的菁英阶层,以及国际援助上,因而采取的策略进程,往往是失根的,受外界所主导的,在具体的实施措施上,亦往往缺乏在地化,没有或缺少本地的声音,进而无法进一步发展出本地的草根运动。纵使有诸多宣称可以赋权的作法,都因为缺乏受害者的直接参与,使得发言权被转型(期)正义的非政府组织所把持,受害者不得不依附于这些组织下,任令其为他们代言。转型(期)正义在作法及理念上应更具转型正义。
究竟何谓转型正义?简单来说,这系以转型(期)正义作为对立物所得出的,「转型正义并不寻求完全取消或取代转型(期)正义,但它确实企图彻底地改革它的政治、位置及优先顺序。转型正义意味着焦点的转移,从法律到社会及政治,并且从政府及机构转到社群及日常的关切。转型正义并不是一个外在法律的架构或是机构的模型由上而下的结果,而是一个由人们的需要及生命的分析和理解出发,由下而上的过程。与之相似,转型正义的工具不会侷限在转型(期)正义的法庭及真相委员会,而会由能够影响更多涉利者的社会、政治及经济的政策及措施来组成。」
从性别和原住民这些在转型(期)正义中较少被触及的领域为例,便可以看出促使转型(期)正义进一步转型的重要性。
性别与转型正义
有关于战争的质性和量化研究均显示,战争是高度性别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伤亡的人百分之八十是军人,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只有近半是。当越战时,只有百分之二十是军人。其他的全是平民,其中最主要是妇女和孩童。性别暴力往往更常出现在内战中,以刻意羞辱对战的另一方男性无法保障自己族群的女性。
Richard Payner、J. Pettman及R. Rayner等人更主张,军事训练涉及高度男性气概的社会化历程。年轻的士兵往往透过与娘娘腔等阴性特质的切割,来证明自己是个好军人。这往往涉及对年青男人在性方面的不安全感及性身分认同来达成。与性侵害极其相关的男性迷思,特别是性角色扮演的刻版印象,同对女人的敌意,或对性暴力的认同与接纳,便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
可惜的是,专门内来处理后冲突的转型(期)正义,不论是司法审判,抑或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却因为采取某种性别中立的立场,而往往无法全面地呈现妇女人权的大规模侵害现象。纽伦堡及东京战犯法庭完全未提及战争中的强暴及慰安妇等议题,便是一例。这个情况一直要到在1990年代以降,跨国女性主义者开始关切冲突中性暴力的法律处置议题,才获得改善。
国际社会相关法律的改变,主要在三方面: 首先,要确认妇女在武装冲突中所遭受的性别暴力被列为严重的战争罪行名单中,这意味着,将性犯罪视为是违反人类罪行,种族灭绝,更是对日内瓦条约(Geneva Conventions)的严重背离。国际刑事法庭更明确将强暴、性奴隶、强迫援交,怀孕、绝孕以及其他的性暴力视为是战争罪,人口贩卖亦被包括在违反人类的罪行中。其次,是协调这类型的战争罪行在法律标准与起诉实务上的落差,这主要是在检讨有关于战争罪行该如何进行调查,以及可以援引哪些条例来征询专家意见等等。最后,推动法庭审理程序的改革,避免对受害者造成二度伤害,包括调整证据法则,禁止使用受害者过去的性行为作为佐证,取消对受害者证词的查核,以及限制使用知情同意作为性侵害辩护的理由等等。
无奈的是,法庭审理之外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乃至相关的补偿条例等机制,经常亦是假借着某种性别中立的立场,有意无意将妇女排除在外。这导致在战争后对妇女的父权打压往往再次复辟,在有关于政府如何转型,以及转型成为怎样的社会的过程中,妇女往往遭到排挤。
后来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机制因而采取了三种修正的作法,以便让其更具有转型正义,像是采用性别主流化的理念在所有的运作上,从相关人员的培训到招募等,或是成立特别的单位主要来负责性别相关议题,作出报告,并进行具性别正义视角的分析与判读,或是结合上述二者的折衷作法。
被拿来和智利及阿根廷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来作对比,视为是某种具性别平等指标的南非,就针对性暴力的受害者采取了比较特殊的安排,诸如: 容许他们不必公开作证,证词也保密,在清一色女性或由妇女团体所组成的、不对外公开的听证会作证。其实,这在当地的女性主义者眼中,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像是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过窄地定义对人权的侵犯在对个人公民及政治权利上,特赦的相关要件很难适用在性侵害案件中,以及一开始未能根据性侵害事实常导致受害方遭到排挤与污名化的社会文化脉络,设计出对受害者友善的审理环境,凡此种种导致受害者不敢述说,加害的男性无诱因认罪,乃至社会父权意识越发地根深蒂固的情况。
犹有甚者,在黑白严重对立的氛围下,不少黑人女性遭受到的性暴力其实不单来自白人,也有不少来自自己黑人「非洲国民议会」(ANC)的同志。不少黑人女性噤声,或是害怕揭露自己的遭遇,会被视为是背叛出卖,被自己所属的政党及族群排斥,或是担忧如今己上位的加害者会对她们采取报复性作为,或是害怕在父权的社会氛围下,加害者非但无法遭定罪,自己反倒毁了从政生涯的未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Rita Mazibuko的遭遇变成了沉默文化规训不听话的女性绝佳的范例。Rita Mazibuko曾在流亡时遭到多位ANC同志的性侵,并获得另一些男同志如Mathews Phosa的帮忙。但当时任省长的Mathews Phosa劝她不要出来作证,否则他会为了捍卫ANC的缘故,否认这件事。不顾劝阻的Rita Mazibuko离开证言台时,是挫败的,一位学者这样描述,「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她控诉时不发一言。没有一个委员,甚至没有一个捍卫女权的女性主义者,站起来说,『我们尊重Rita Mazibuko 按著自己所知的述说的事实,正如我们尊重Mathews Phosa的一样。但我们期待他也能出来作证。』」
原住民与转型正义
正当转型(期)正义逐渐扩及其他未经历转型期的社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补偿等机制,被用来处理大规模的人权违犯事件,不知不觉地将西方自由主义下的民主社会视为可欲的标的,转型(期)正义「却忽略了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本身,也需要在后冲突的复和与修复式正义的框架下,加以审视」。
因而,尝试用转型(期)正义来处理原住民正义的诉求,往往会在三个面向上遇到政府与原住民社群的冲突,转型(期)正义本身不但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甚至成为政治争端。首先,究竟转型(期)正义要处理的时间起迄点如何界定。其次,政府可能诉诸历史及当前合法政策来划定转型(期)正义的合理界线,而原住民社群却想要用过去来批判现今的政策。第三,政府会意图使用转型(期)正义来确认主权与法律正当性,但原住民社群却会抗拒这样的策略,甚至作出不同的有关于主权及法律正当性的宣称。
不过,近来在实务上,随着加拿大及澳洲政府尝试以转型(期)正义来解决原住民人权争议,不少原住民社群在争取原住民人权的诉求时,也开始有条件诉诸转型(期)正义的法律框架。所谓的有条件,一方面是带着高度文化敏感度的,特别是针对转型(期)正义往往会强化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典范这点,另一方面是争取主导权,以便用更具转型正义的作法,比如说在个人人权之外,要求像是自治、土地等集体权利,来修正转型(期)正义。
Jennifer Balint, Julie Evans and Nesam Mcmillan等学者便受到诸如女性主义转型(期)正义理论的影响,一方面,用结构性不义来界定殖民历史带来的伤害,一方面引用Iris Marion Young的理论,要求转型(期)正义应该超越对加害者个人或政府的究责与补偿作法,更深入分析历史创伤所带来的结构性不平等后果,并对更深层的、范围更大的改革,抱持开放的态度,甚至考虑纳入原住民传统司法,来全面促进社会、政治、法律乃至经济的转型。
以土地为例。原住民族其实肯认他们祖先的土地如今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和他人共享,只是这样的共享必须是建基在平等的基础上。由于土地对原住民文化传统及族群的延续至关重要,而移民往往对原住民族群的生计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因此,必须对相关的开发作出限制。当然,对于怎样才构成平等基础,原住民与移民有不同的界定,需要作出更多的协商。而协商就住一步涉及到双方不同的期待。由于原住民族土地的归还,伴随着的是期望得以维持原住民自治,所以土地不是单单归还给个别的所有权人,更要考虑到族群如何在成员个人及群体的权利与义务间达到某种平衡。这使得引入原住民传统司法,显得更加重要。
教会可以扮演的角色
台湾有关于二二八及白色恐怖的历史记忆虽然不缺女性,但却多以受害者家属的身分被记忆。妇女是否因为结构的不义而遭到性侵害,或沦为社会经济的弱势?性别该如何纳入转型正义的机制中,落实一个具性别公义的新国家?
另一方面,蔡英文总统就任后,曾代表国家为历代殖民政权迫害族人和土地流失,向台湾的原住民族道歉,并宣示总统府将设置「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来推动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不料,去年2月14日由原民会公告的「划设办法」,因考量到宪法保障私有财产权,将原住民族传统领域中现今的私有地排除在外,让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硬生生少掉近百万公顷。原住民族为此强烈抗议,在凯道上露宿至今,抗争犹在持续中。如何让转型(期)正义在性别和族群的议题上真正发挥转型效应,这些问题的探讨,在台湾犹在起步阶段。
教会,做为台湾社会的一份子,在强调在地化、由下而上的深层转化的转型正义中,理应能够扮演更形重要的角色。举例来说,社群权责(Community accountability),便是以社群团体(朋友、家族、职场、邻舍,包括教会在内)为中心所发展出的一种转型正义的策略,旨在让社群被组织和动员起来,去促成几件事: 首先,创造并肯认相互支持及关怀的社群价值,并且拒绝侵害和压迫,进而,采取积极作为,提供受暴力攻击的社群成员安全及支持的网络,并尊重他们的自主决定,再进一步发展出长期的策略去对治社群加害者的恶行,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加以转化,最终,落实社群的政治结构的翻转。然而,要推动社会转型正义的教会,必须从自身做起,先从内部的转型开始,真诚面对过往与威权体制的历史,现存的性别及族群歧视,以及教会政治中未尽民主的代议结构。
(Photo credit: Nomad@Live / CC BY-NC-ND)
传扬论坛期待透过每篇文章激发更多基督徒思考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不断重新理解上主在这个世代的心意。 面对艰困的媒体环境与难以质疑、反省的教会文化,我们没有教派包袱,愿在各个公共议题上与大家一同反思。 为维持平台运作,传扬论坛每个月需要15万元经费,祈请兄姐关心代祷及奉献,与我们同行,并向更多人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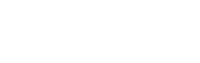
除非全然更新,所谓革命,也就是转型正义。否则政党轮替只是新瓶装旧酒,绿正义取代蓝正义,政权转移换人享受权力而已,本质毫无变化,只是多了转型期正义的「改革」把戏,下回2020政党若再次轮替,换人抬出转型期正义报复性的「改革」。无论性别、种族、劳工、贫富或新生代前途等等问题都成「改革」戏码。街头抗争成为台湾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光特色。
总之坏树结不出好果子。有谁能把台湾这欉番薯重新换种好种?才是所有住在台湾的人之期待。至于教会若不重生,权力之酵不除,有能力的基督徒若不从政,教会仍是无可救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