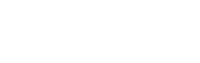行政院日前分別公布促轉會正副主委與專兼任委員名單。由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及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等多個民間團體共同組成的「監督促轉會聯盟」旋即透過提問促轉會委員,敲鐘震虎,希望在就任後選前承諾屢屢跳票、甚至啟用具爭議性黨國舊臣的蔡英文政府不要打假球。
其中,針對張天欽副主委提名人的特別提問,「為了可以繼續逮捕匪諜,將前述法網(第68號及80號解釋)延伸到14歲以下的第129號解釋。……促轉會在處理司法平反案件時, 如發現類此的司法解釋有違『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可否移請司法院廢棄相關解釋或判例」,切中了國共內戰時期強行征招未成年入伍的史實。據說,當年駐紮在江西寧都一帶的少共國際師1萬多人,平均年齡只有18歲。年齡最小的紅軍,更是只有9歲。
雖然當時到底有多少人因適用第129號解釋而入獄,不得而知。但這並沒有使得這項提問顯得無足輕重,相反地,因為它涉及台灣在轉型(期)正義的相關討論中甚少提及的兒童人權,而更值得深入探究。到底兒童在轉型(期)正義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可以說,兒童是受害最深,卻最晚才獲得論及的轉型(期)正義相關涉利者。兒童因為年輕,無知,容易受人恫嚇,或受家庭經濟等壓力,而常成為殺害、刑求、綁架,及強迫招募,甚至性暴力的受害者。猶有甚者,由於社會價值規範解體,兒童的加害者不單單來自敵對的陣營,還可能是己方的成員,甚至可能是生命成長歷程中的重要他者──家人。這使得還原歷史真相,備加不易,他們或是擔心受到排擠和污名,或是不忍心讓親人站上刑台,而選擇沈默。凡此種種導致武裝衝突或軍事統治時期,兒童受到的衝擊不單侷限在公民政治相關權益,更波及至經濟、社會、教育及文化等層面。縱使社會轉型,其後續的心理創傷效應,亦可能長達終生之久。
無奈,兒童慣常不被視為是權利的主體,沒有發言權,所以,在轉型(期)正義的討論中,一直要到2002年,隨著國際刑事法庭的成立,聯合國兒童基金(UNICEF)出版了《國際刑事司法及兒童》(International Criminal Justice and Children),方才獲得正視。
現今普世的共識是,未將兒童納入轉型(期)正義中,不僅違反了《兒童人權公約》,更會嚴重阻礙社會全面轉型的進程。而如何保障兒童也可以參與在轉型過程中,獲得司法平復,或是咎責,乃至於與自己與社會復和,重建健全、具尊嚴及信任的人際關係網絡,進而促成社會的長遠和平,是論及兒童人權與轉型(期)正義的學者至為關心的。
咎責?沒有錯。雖然,一方面,兒童無可避免是受害者,另一方面,更加殘酷的事實是,他們未必真的那樣無辜。童兵就是個明顯的例證。兒童被招募入伍,幾幾乎是屢見不鮮的事!這就是為什麼國際刑事法庭的《羅馬規約》第8(2)(b)條便明定,「徵募不滿15歲的兒童加入武裝部隊或集團,或利用他們積極參加敵對行動」犯戰爭罪。1989年的《兒童人權公約》雖明定未滿18歲者為兒童,但卻在第38條主張,「締約國應採取所有可行措施,確保未滿15歲之人不會直接參加戰鬥行為。……在招募年滿15歲但未滿18歲之人時,應優先考慮年齡最大者。」要到了2002年,公約的附加議定書生效,才規定「各國應盡全力保證15至18歲公民不直接參與任何軍事武裝活動並不會被迫徵召入伍。」
兒童軍人,其中有男,也有女。在一些國家,女孩的比例甚至高達百分之25,除了直接參與作戰,其職責也包括了照顧傷患、炊事,洗衣,採集食物,有時甚至包括強制婚姻(forced marriage),或性奴隸。正是因為童兵年幼,服從性高,往往輕易犯下令人髮指的不人道罪行。過去在轉型(期)正義的相關文獻中,常常不假思索地將他們直接認定作是「無過失的被動受害者」(faultless passive victim),把女孩刻板印象化為發育不全懵然不知的可憐性奴,男孩則是手持長槍一臉稚嫩的娃娃兵,顯然是不正確的作法。
Kieran McEvoy和Kirsten McConnachie 便主張,從1970年代以降,以操弄受害者身分而出現的各式政治動員,採取這樣一種「受害者政治」(the politics of victimhood)立場,視加害者與被害者分別隸屬二個相互對立的社會範疇,加害者是作為禽獸的「他們」,受害者則是無辜的「我們」。這種二分法在訴求制定政策去保障「受害者人權」並嚴懲加害者的同時,無形中為受害者形塑了投國所好的刻板印象──「真正的」受害者必須是「無辜的」、必須也「要求嚴刑重罰」。如果受害者不是這樣表現,那他就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某種程度上「算是自作自受」,是「活該的」,自然也無權要求什麼法律的正義。
無辜的受害者,當然不是沒有,但非常少。要命的是,他們被不當地挪用為集體象徵,從而形構出相關的「正邪不兩立」的敘事,最終只為了成就我們堂而皇之的居於道德制高點。
偏偏童兵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根本不符合這樣的「受害者神話」。實證研究者甚至發現,很難用自願或是被迫這樣簡化歸因的方式,來描繪受訪童兵的真實動機。
與其用對立的範疇來分類轉型(期)正義過程中的個人參與,倒不如用光譜或受害者的階序來形構他們之間的關係。事實是,在轉型(期)正義所要處理的結構性罪惡下,絕大多數的受害者,都是所謂的「壞受害者」,或多或少參與在出賣,或不法利益交換中。Pimo Levi便指出,即便在納粹的集中營,複雜的權力網絡,使得個人無法單單被劃為受害者或加害者,特定的猶太人往往被納粹黨衛隊指派做監管的工作。曾被囚禁在集中營的意義治療大師Vicktor Frankl在其回憶錄《活出意義來》(Man’s Search for Meaning)稱這些人為「酷霸」,不僅常仗勢欺壓自己的猶太同胞,敲詐勒索,甚至親自送他們走上黃泉路。相類似的情況,亦出現在南非、獅子山、阿根廷及北愛爾蘭等地。
這並不是要否認加害者個人或其群體的可責性,而是讓轉型(期)正義得以更加接近歷史的真相,更能多一些悲憫、少一些報復。也正是因為如此,縱使兒童在轉型(期)正義的參與深淺及方式,往往依不同文化脈絡而定,但多採取不具備刑事審判意涵的、非以追究罪責為主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以及其他復和的傳統法律慣習。
由於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或其他的作法,往往由政治勢力所操控,2008年由聯合國兒童基金及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公室(OGCHR)所舉辦的工作坊中,一些兒童參與者反對由政客成立委員會來調查真相,並抗議真相為政治目的服務,轉而提出使用公開討論、戲劇、音樂及藝術等形式,來表達兒童的觀點,以促進復和。此舉或許可以避開法學界對於兒童證詞的可信度,以及兒童出席法庭審理會否造成二度傷害,對其日後心理健康影響的相關疑慮。
到底該怎樣根據「兒童最佳福祉」來規劃轉型(期)正義的機制?目前並沒有一定的共識。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出於保護的心理,拒絕對兒童進行採證,或容許其出席公聽會。但5年之後,2001年,獅子山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卻主張,兒童可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中出席作證,惟應在程序上更加保障其隱私。利比亞隨後亦採取相同的作法。然而,爭議仍舊存在,在肯定兒童的主體性及參與發言權益的同時,如何設立保護性措施,以避免他們處身在超過其年齡所能負荷的心理危機中?轉型期的社會像是踩在一條狹窄的紅線上,輕易便可能越界,造成兒童的二度傷害,像是在交互詰問時,致令他們經受不住壓力,而否認先前作出的證詞,或是遭控方逼問,去承認自己殺害或強暴過父母或親人,抑或是去承擔他們無法面對的嚴厲刑責,進而導致其成功復歸社會的希望破滅。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政治的全面轉型要能成真,和平與社會重建要能持久,兒童,社會未來的主人翁,理應有份於轉型(期)正義。誠如前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主席,己故的南非大主教屠圖(Desmond Tutu)所言,「兒童……具有超乎尋常的能力可以洞察事物,可以揭露出事物本來的恥辱和欺瞞。」
傳揚論壇期待透過每篇文章激發更多基督徒思考信仰與社會的關係,不斷重新理解上主在這個世代的心意。 面對艱困的媒體環境與難以質疑、反省的教會文化,我們沒有教派包袱,願在各個公共議題上與大家一同反思。 為維持平台運作,傳揚論壇每個月需要15萬元經費,祈請兄姐關心代禱及奉獻,與我們同行,並向更多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