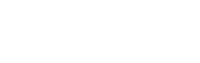中國海內外民主運動的「冰凍」狀態
2016年6月4日晚上,在華府的中國駐美大使館外面的廣場(未來有可能被命名爲劉曉波廣場),中國的政治流亡者們舉行一年一度的紀念六四晚會。
按照慣例,第一個演講的嘉賓是自詡為「中國民主之父」的魏京生。魏宣告,中共的統治即將崩潰,民主運動形勢一片大好。他舉出一個事例來證明:有一次,他在馬里蘭一家中餐館吃飯,正好來了一個中國旅行團。其中,有一對中年夫婦走過來對他說:「您是魏先生嗎?我們都很敬重你。國內民不聊生,我們希望你回去拯救大家於水火之中。」那一瞬間,魏京生似乎成了新時代的孫文——100多年前,在美國的孫文也日夜盼望著中國發生起義的消息。孫文盼來了並不是他策劃的武昌新軍的起義,魏京生能否能盼來他的武昌起義呢?
我相信魏先生的誠實,他講述的故事大概不是他刻意編造的。但僅僅靠這個故事能說明中國的人心所向嗎?我無法苟同。據近期統計數據表明,中國第一流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學生中,共產黨員的比例越來越高,全國黨員人數也在攀升,而不是像蘇聯解體前幾年那樣,共產黨每年流失數百萬黨員。不得不承認,中共仍然強大,仍然有相當的民意基礎,不是在海外喊幾聲打倒就能打倒的。
習近平執政以來,江胡時代容忍一定程度公民社會的「韌性威權」已經消失,提出這個概念的美國學者黎安友表示,習近平時代不適用於「韌性威權」的概念。台灣學者徐斯儉和王占璽在論文《消失中的威權韌性:習近平時期的國家社會關係》中指出:在鞏固黨國領導權威上,習近平強調黨的絕對領導,並在意識形態上反撲、否定西方價值;在官僚體系的改造上,以反腐為名清洗敵對派系,將中紀委塑造成現代錦衣衛;在社會控制上,強勢而持續地打壓被他認為具有威脅性的社會力量,以此在社會部門創造寒蟬效應——江胡時代對「不穩定力量」是「定點清除」,只選擇代表性人物進行打擊,如民主黨的組黨活動、法輪功的抗議、《零八憲章》運動(即便是《零八憲章》運動,被抓捕並判刑的只有劉曉波一個人);但在習近平時代,打擊則從「點」轉向「面」,如對維權律師群體的全國性大抓捕,是一次性地將最危險人物、危險人物和次危險人物全部抓捕。江胡時代出現雛形的公民社會以及維權力量,遭受重創、土崩瓦解,用一名身在其中的人士的說法就是:人權活動者被抓捕,爲他們辯護的維權律師被抓捕,爲維權律師辯護的同行被抓捕,然後是他們的家人遭到連坐懲罰,於是全國一片鴉雀無聲。
在此嚴峻形勢之下,中國中產階級審時度勢,安於現狀,推動社會變革的意識非常薄弱。美國《政治研究季刊》(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發表了學者陳捷題為《中國的民主化和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民主態度》的論文,這篇文章以大量的抽樣問卷調查數據爲支持,回答了人們非常感興趣的問題「中國城市的中產階級在何種程度上支持基本的民主價值和制度?」文章認為,一方面,和大部分下層階級的民眾一樣,大多數中產階級對與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個人權利很警醒。然而,另一方面,當這些權利「有可能會」破壞社會秩序時,大部分中產階級都不願意行使其政治權利;他們沒有意願對政府事務發表意見以及在政治變革中發揮作用;他們似乎只支持當前一黨主導和控制的選舉制度下的差額選舉。從比較視角來看,城市的中產階級在整體上對民主原則和制度的支持度不如下層階級。陳捷的研究結果表明:儘管中產階級或許「希望有一個相互制衡的制度來有效地約束黨的權力」,以免自身的經濟和社會利益受損,但他們並不樂意支援和參與促進民主的政治變革。
就海外民主運動來說,我的看法不是形勢大好,而是處於某種可悲的「冰凍」狀態。海外華人主流社會基本不認同海外民主運動。清末時,流亡海外的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為和梁啓超,革命派代表人物孫文和黃興,在日本、東南亞、美國和歐洲獲得海外華人的熱情支持,包括資金捐助——那時海外華人大多是處於社會底層、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苦力。而今天的海外華人,相當一部分是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到西方留學、獲得較高學位並定居的專業人士和中產階級,甚至有數十萬人是「六四綠卡」的受益者。然而,他們對海外民運普遍持負面看法,支持民運者寥寥無幾。
海外民主運動的邊緣化、泡沫化,當然有中共特務搗亂、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以及海外華人再國內有參與、且對國內親友的安全有顧慮等原因,但民主人士自身的弱點和缺陷也不容迴避。由於沒有更高的信仰及道德標凖,民主運動日漸淪為對有限資源的爭奪,以及由此造成的彼此之間的謾罵和攻擊。
長期的流亡生活,讓魏京生等曾被西方追捧的標誌性人物,逐漸被人遺忘,最後他們只好靠不切實際的幻想麻醉自己。有一個笑話說,在紐約法拉盛,街頭行走的人當中有超過一百位未來中國的總統和總理。其實,這不是笑話,那些人確實認真地認為自己是未來中國的總統和總理,甚至擬定「影子內閣」名單。有一名自封爲總統的人,嚴肅地對某位追隨者說:「以你的才能,不能當部長,只能當副部長。」有一個自稱「中國過渡政府」的組織,定期發佈所謂的「政府文告」,宣佈「通緝」中共政權現任領導人。權力是春藥,虛幻的權力也是春藥。
在紐約法拉盛這個美國最大的華人聚居地,存在著幾十個形形色色的反對黨組織,人們很難從名字上分辨其政治綱領的差異。號稱「民主黨」的組織就有好幾個,需要在後面的括號之內標註出彼此的不同(就好像台灣台中的特產「太陽餅」,一條街上有數十家太陽餠店鋪,每一家都聲稱自己是正宗創始店)。很多反對黨辦公室的樓上都有律師辦公室,黨組織和律師聯手辦理一條龍的「政治庇護移民」服務:那些來自福建等地的偷渡客,支付數千乃至數萬美金,註冊成其黨員,然後由該政黨安排一群偷渡客去中國使領館抗議,黨證和錄影就成為其辦理政治庇護申請的關鍵文件。或許,得不到華人社群捐款支持的政黨只能通過這種方式掙錢才能生存下去。但是,正如劉曉波所說,民間力量跟共產黨抗爭,既沒有錢,也沒有武器,惟有道義。如果連道義都沒有了,還能剩下什麽呢?一個靠爲偷渡客辦假政治庇護而生存的海外反對黨,到了未來中國民主化的那一天,還有可能回中國去參選甚至執政嗎,它拿什麽來取信於民呢?
對於很多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來說,民主或自由主義並不能成為生命的支柱,曠日持久的壓迫、疏離、孤獨和邊緣化,會讓他們選擇放棄乃至背叛自己的初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80年代的改革派知識分子甘陽。六四屠殺之後,甘陽流亡西方,曾在芝加哥大學求學,因攻讀博士學位受挫而對西方充滿仇恨。後來,甘陽赴香港大學任教,成為反西方的、民族主義的吹鼓手。他炮製出「打通三個中國偉大傳統」的理論,希望被最高當局採納。所謂「三個傳統」,即孔子的儒家傳統、毛澤東的社會平等的傳統、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傳統。然而,這三傳統自相矛盾、彼此對立:毛澤東時代曾批判孔子,派紅衛兵砸爛孔廟、發掘孔墓;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對毛澤東來說則是修正主義、是叛徒。甘陽爲了被中國政府寬恕並重用,匆匆獻上「通三統」理論作為投名狀,完全顧不上修補這些學理上一目了然的漏洞。近年來曾經紅極一時的反對派名人如焦國標、艾未未等人也走上了「殺人放火被招安」的老路。
喬治·歐威爾在《動物莊園》中的最後一句話是:「窗外的動物們先看看豬,再看看人,又反過來先看人,後看豬,但他們再也分辨不出人和豬有什麼分別了。」當反抗者變得跟反抗的對象一模一樣,反抗還有什麽價值呢?
讓基督教保守主義像光一樣照亮反對運動
那麽,中國反對運動的出路何在?中國如何開啓未來的民族轉型之路?中國家庭教會以及在家庭教會中成長起來的基督徒保守主義者、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可以在其中扮演什麽樣的角色?
近年來,加爾文神學及保守主義政治哲學,進入中國城市新興教會。加爾文認為,神學是一種「實踐科學」,他自始至終都致力於從神學的視野思考法律和政治觀,他比馬丁·路德更積極地強調上帝的律法對基督徒生活和公共政治的指導和約束——一切拓展人類自由的事業方面,教會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基督教的重要價值是「讓被虜的得自由」。德國神學家莫特曼指出,「上帝」這名字應許從罪惡和死亡中得自由是我們無盡的自由。從政治性的奴隸制度「出埃及」,進入應許之地,在舊約傳統中佔據核心地位;被釘十字架的基督復活,進入永遠自由的國度,在新約傳統中佔據核心地位。基督徒相信基本的價值觀,如人性尊嚴、人身自由、人權等,都是源自創造萬物的上帝。自由是上帝賜予人類的禮物,不能讓這個寶貴禮物被獨裁者無緣無故奪走。放棄自由,就意味著人忘記了人是上帝按照其形象造的;放棄自由,就意味著人玷辱了上帝賦予的「治理全地」的權柄。使徒保羅說:「你們是重價買來的,不要作人的奴僕。」基督徒不能安於被奴役的狀態,教會也不能成為政權的奴僕。
以改革宗信仰出發,教會必然是一種公共性的存在,個人的信仰必然是一種整全性的生活方式。歸正信仰不主張採取「屬靈」與「屬世」完全對立的、一刀兩斷式的二分法,而主張基督徒既是天國的子民、又是地上的公民。信徒對教會有委身,教會對社會有責任。教會要成為抵擋和糾正錯誤的時代潮流的中流砥柱。教會具有獨立和超然的地位,如果教會像牆頭草一樣隨風而動,便背離了上帝的真道;如果教會成為政權手中的籌碼,信仰那超越性的價值便無法持守下去。
在教會的歷史上,曾經有過若干血的教訓。比如在納粹剛剛開始興起時,德國教會假裝沒有看見納粹迫害猶太人等罪惡行徑,爲「反正納粹殘害的不是我們」而暗自慶幸;當納粹向教會伸出黑手時,教會已經沒有招架之力,只好乖乖地臣服於希特勒的淫威之下。以生命殉道的潘霍華牧師嚴厲批評說:「我們的教會在這些年只為自己的存留而奮鬥,好像這才是主要的目的,這樣的教會沒有能力成為世界的代言人,為人們講出和解及拯救的話語。」他強調,基督徒不能單單安享上帝的恩典而對外面的世界閉目塞聽:「由於基督承擔起我們的重擔,所以我們應當擔負起同伴的重擔。基督的律法就是背十字架,這也是我們要完成的任務。」
中國海內外民主運動陷入低潮,原因之一是:「民主」無法形成一種永恆性的信仰,它只是權力和社會資源的分配方式,只是諸多社會運行模式中「最不壞」的一種,它甚至比不上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更有號召力。反對運動需要更高的信仰提供意義和價值,基於基督信仰的保守主義價值觀可以像光一樣照亮反對運動。
從基督教中尋找力量和精神源泉的抗爭者越來越多。劉曉波將基督教信仰當作精神支柱。早在80年代中期,劉曉波就從研讀康德進入基督教文化,他認為:「中國的悲劇,是沒有上帝的悲劇。」他在天安門運動之前計劃出版的一本書,就名為《赤身裸體,走向上帝》。此書還未上市就被銷毀。劉曉波在獄中最喜歡讀的是奧古斯丁的《懺悔錄》。中國的知識分子大都傳承傲慢自大的儒家人格,號稱「內聖外王」;劉曉波是其中少有的、具有基督教「懺悔精神」的人。他從不認為自己是英雄或聖徒,而認為自己是「可恥的倖存者」。當他因《零八憲章》被中共判處11年重刑時,他在法庭上的最後答辯詞名為「我沒有敵人」;當他獲知自己榮穫諾貝爾和平獎時,他對前來探監的妻子劉霞說,這個獎是給「六四」受難者的。這種反抗者的謙卑,在中國反對派領袖中十分罕見。
劉曉波與90年代後期興起的家庭教會保持著密切聯繫。當我所在的北京方舟教會受到警察騷擾時,他撰文加以聲援,讚揚信徒們的非暴力抗爭手段:「基督徒甘願承受苦難的良知反抗的偉大之處就在於,當人類必須面對被強加的暴政及其苦難之時,居然是受害者心懷謙恭而尊嚴的愛意,主動邀請加害者回到仁愛、寬容、理性、和平的規則中來。而神意的回歸,必將通過殉難的持續累積(接力式反抗)和極端受難形式(被釘十字架)對施害者的靈魂構成的巨大壓力。作惡者施暴的強度與受難者抗暴的韌性成正比,所謂基督教的『堅忍主義』,就是用基督徒承受苦難的毅力來對抗迫害者製造苦難的意志,用信仰給予靈魂的力量來抵抗恐怖暴力的肆虐。」
在中國歷史上一以貫之的暴力衝突、改朝換代的模式之外,家庭教會的抗爭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中國不能再發生一次毛氏革命,悲劇的重複就是鬧劇;中國只能學習英國光榮革命和美國獨立革命那樣的「革命」,並以此走出歷代王朝更迭中人相殺、人相食的慘劇。劉曉波概括說:「無論遭遇怎樣的不公正,基督徒的良知既不會訴諸於仇恨和暴力,也決不會屈從於惡法和權勢,而是堅持用愛來融化恨,用善意來喚醒敵對者的良知,用徒手不服從來征服全副武裝,直到良知者忍受苦難的能力消耗盡施暴者的仇恨,最終超越‘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參照南非成功社會轉型(政治領域)的經驗,可以想象,若沒有浸潤在基督教文明中的曼德拉和圖圖主教的不懈努力,若沒有代表人間正義和人類良知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高速運轉,橫亙於不同民族、不同階級之間的暴戾之氣,如何消解?若冤冤相報,這個國家永遠沒有未來。
另一位基督精神的實踐者是2016年8月3日被判處七年半重刑的北京家庭教會長老胡石根。胡石根在「六四」後因參與民主黨組黨活動,被判處20年重刑,坐了16年牢。這一次再度被判重刑,刑期加起來可以「將牢底坐穿」。這一次判刑,檢方將胡石根受洗的照片作為罪證之一,而罪名是「利用宗教力量反對黨和顛覆政府」。
前一次入獄的16年當中,胡石根一直在苦苦思索中國的出路。在世俗政治的黑暗和人性的敗壞中,他看不到任何希望。「我在監獄裡,真的是對中國人陷入絕望。我曾經提出過這樣一個命題,叫『中國孬種』。很多人聽了會不太舒服。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經過將近100多年的奴役,中國人把過去所僅有的一點剛強、勇敢、骨氣,都給消磨了。尤其是經過這60多年的奴化教育,上上下下,幾乎所有人,都變成服服帖帖的奴隸,而且甘心於做這樣的孬種,覺得好死不如賴活著。那時,我覺得不僅個人沒有希望,整個國家都沒有希望。」
一位報導中國真相的記者說過,光明不是由黑暗來定義的,而是由尋找光明的人來定義的。在暗無天日的監獄裡,胡石根驚訝地發現,有一批基督徒獄友和別人就是不一樣,他們謙卑、忍耐、平安、喜樂。於是,胡石根就跟這些基督徒攀談、交往,從他們那裡听到福音,進而被上帝挑選成為基督徒。胡石根在《聖經》中發現了自己的名字:「上帝的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奇妙的是,並不是基督徒的父母親,給他取名時讓他的名字中包含了「柱石」和「根基」的雙重含義。
第一次出獄後,胡石根成為北京一間家庭教會的長老,他在新興城市教會中找到了中國的希望所在:「看到家庭教會的發展,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積極傳福音,看到那一張張洋溢著神的榮光的臉,我又慢慢從絕望中振奮起來。我感到中國還是很有希望的,上帝正在中國施行奇妙的事情。這60年,對中國損害最大的,還不是這個物質財富上的損害,更多的是,是對人心的毒害、對文化的毒害。我們有必要通過福音化,來解決人心的缺失、文化的缺失問題。從而使得我們在爭取民主化的過程中,能夠贏取人心;在鞏固民主化的過程中,能夠凝聚人心。這就是福音化在中國的重要意義。」那幾年裡,胡石根將生命的重點轉向傳福音和建教會,但也沒有放棄參與政治活動,他身體力行地將內在的生命敬虔和影響公共社會兩者融為一體。清教徒時代的信徒就是如此,信仰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發生關係,上帝從來沒有讓基督徒在政治領域缺席。信仰不是政治之工具,信仰卻不能外在於政治而存在。
胡石根如此描述對自己所在教會以及中國家庭教會的熱切期待:「我希望我們這個小小的團契,能夠在查經學習當中,通過禱告,通過分享,通過查經,不僅是在知識上瞭解神學,瞭解基督教,瞭解聖經,更多的是要把我們個人的生命、個人的生活,同主耶穌連結在一起。我們要活出主耶穌基督的生命來,這樣我們的教會就能成為一個主所悅納的教會。我希望更多的家庭教會,現在也許會被稱之為老底嘉那樣的教會,通過跟主建立生命上的聯繫,來變成偉大的教會,在中國基督教興起的時代中,來見證神的榮耀。」
中國並非沒有未來,中國的未來不掌握在共產黨手中,也不掌握在被共產黨意識形態所毒化的、做著皇帝夢和總統夢的「當代洪秀全」、「當代孫大砲」手中,而掌握在劉曉波、胡石根等熱愛自由、堅持公義的知識人和數千萬「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主同行」的家庭教會信徒手中。
(Photo credit: Andrew121215 / CC BY-NC)
傳揚論壇期待透過每篇文章激發更多基督徒思考信仰與社會的關係,不斷重新理解上主在這個世代的心意。 面對艱困的媒體環境與難以質疑、反省的教會文化,我們沒有教派包袱,願在各個公共議題上與大家一同反思。 為維持平台運作,傳揚論壇每個月需要15萬元經費,祈請兄姐關心代禱及奉獻,與我們同行,並向更多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