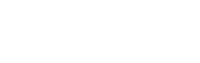中国海内外民主运动的「冰冻」状态
2016年6月4日晚上,在华府的中国驻美大使馆外面的广场(未来有可能被命名为刘晓波广场),中国的政治流亡者们举行一年一度的纪念六四晚会。
按照惯例,第一个演讲的嘉宾是自诩为「中国民主之父」的魏京生。魏宣告,中共的统治即将崩溃,民主运动形势一片大好。他举出一个事例来证明:有一次,他在马里兰一家中餐馆吃饭,正好来了一个中国旅行团。其中,有一对中年夫妇走过来对他说:「您是魏先生吗?我们都很敬重你。国内民不聊生,我们希望你回去拯救大家于水火之中。」那一瞬间,魏京生似乎成了新时代的孙文——100多年前,在美国的孙文也日夜盼望着中国发生起义的消息。孙文盼来了并不是他策划的武昌新军的起义,魏京生能否能盼来他的武昌起义呢?
我相信魏先生的诚实,他讲述的故事大概不是他刻意编造的。但仅仅靠这个故事能说明中国的人心所向吗?我无法苟同。据近期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第一流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越来越高,全国党员人数也在攀升,而不是像苏联解体前几年那样,共产党每年流失数百万党员。不得不承认,中共仍然强大,仍然有相当的民意基础,不是在海外喊几声打倒就能打倒的。
习近平执政以来,江胡时代容忍一定程度公民社会的「韧性威权」已经消失,提出这个概念的美国学者黎安友表示,习近平时代不适用于「韧性威权」的概念。台湾学者徐斯俭和王占玺在论文《消失中的威权韧性:习近平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中指出:在巩固党国领导权威上,习近平强调党的绝对领导,并在意识形态上反扑、否定西方价值;在官僚体系的改造上,以反腐为名清洗敌对派系,将中纪委塑造成现代锦衣卫;在社会控制上,强势而持续地打压被他认为具有威胁性的社会力量,以此在社会部门创造寒蝉效应——江胡时代对「不稳定力量」是「定点清除」,只选择代表性人物进行打击,如民主党的组党活动、法轮功的抗议、《零八宪章》运动(即便是《零八宪章》运动,被抓捕并判刑的只有刘晓波一个人);但在习近平时代,打击则从「点」转向「面」,如对维权律师群体的全国性大抓捕,是一次性地将最危险人物、危险人物和次危险人物全部抓捕。江胡时代出现雏形的公民社会以及维权力量,遭受重创、土崩瓦解,用一名身在其中的人士的说法就是:人权活动者被抓捕,为他们辩护的维权律师被抓捕,为维权律师辩护的同行被抓捕,然后是他们的家人遭到连坐惩罚,于是全国一片鸦雀无声。
在此严峻形势之下,中国中产阶级审时度势,安于现状,推动社会变革的意识非常薄弱。美国《政治研究季刊》(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发表了学者陈捷题为《中国的民主化和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民主态度》的论文,这篇文章以大量的抽样问卷调查数据为支持,回答了人们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中国城市的中产阶级在何种程度上支持基本的民主价值和制度?」文章认为,一方面,和大部分下层阶级的民众一样,大多数中产阶级对与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个人权利很警醒。然而,另一方面,当这些权利「有可能会」破坏社会秩序时,大部分中产阶级都不愿意行使其政治权利;他们没有意愿对政府事务发表意见以及在政治变革中发挥作用;他们似乎只支持当前一党主导和控制的选举制度下的差额选举。从比较视角来看,城市的中产阶级在整体上对民主原则和制度的支持度不如下层阶级。陈捷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中产阶级或许「希望有一个相互制衡的制度来有效地约束党的权力」,以免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受损,但他们并不乐意支援和参与促进民主的政治变革。
就海外民主运动来说,我的看法不是形势大好,而是处于某种可悲的「冰冻」状态。海外华人主流社会基本不认同海外民主运动。清末时,流亡海外的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革命派代表人物孙文和黄兴,在日本、东南亚、美国和欧洲获得海外华人的热情支持,包括资金捐助——那时海外华人大多是处于社会底层、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苦力。而今天的海外华人,相当一部分是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到西方留学、获得较高学位并定居的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甚至有数十万人是「六四绿卡」的受益者。然而,他们对海外民运普遍持负面看法,支持民运者寥寥无几。
海外民主运动的边缘化、泡沫化,当然有中共特务捣乱、中共的民族主义宣传以及海外华人再国内有参与、且对国内亲友的安全有顾虑等原因,但民主人士自身的弱点和缺陷也不容回避。由于没有更高的信仰及道德标凖,民主运动日渐沦为对有限资源的争夺,以及由此造成的彼此之间的谩骂和攻击。
长期的流亡生活,让魏京生等曾被西方追捧的标志性人物,逐渐被人遗忘,最后他们只好靠不切实际的幻想麻醉自己。有一个笑话说,在纽约法拉盛,街头行走的人当中有超过一百位未来中国的总统和总理。其实,这不是笑话,那些人确实认真地认为自己是未来中国的总统和总理,甚至拟定「影子内阁」名单。有一名自封为总统的人,严肃地对某位追随者说:「以你的才能,不能当部长,只能当副部长。」有一个自称「中国过渡政府」的组织,定期发布所谓的「政府文告」,宣布「通缉」中共政权现任领导人。权力是春药,虚幻的权力也是春药。
在纽约法拉盛这个美国最大的华人聚居地,存在着几十个形形色色的反对党组织,人们很难从名字上分辨其政治纲领的差异。号称「民主党」的组织就有好几个,需要在后面的括号之内标注出彼此的不同(就好像台湾台中的特产「太阳饼」,一条街上有数十家太阳餠店铺,每一家都声称自己是正宗创始店)。很多反对党办公室的楼上都有律师办公室,党组织和律师联手办理一条龙的「政治庇护移民」服务:那些来自福建等地的偷渡客,支付数千乃至数万美金,注册成其党员,然后由该政党安排一群偷渡客去中国使领馆抗议,党证和录影就成为其办理政治庇护申请的关键文件。或许,得不到华人社群捐款支持的政党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挣钱才能生存下去。但是,正如刘晓波所说,民间力量跟共产党抗争,既没有钱,也没有武器,惟有道义。如果连道义都没有了,还能剩下什么呢?一个靠为偷渡客办假政治庇护而生存的海外反对党,到了未来中国民主化的那一天,还有可能回中国去参选甚至执政吗,它拿什么来取信于民呢?
对于很多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民主或自由主义并不能成为生命的支柱,旷日持久的压迫、疏离、孤独和边缘化,会让他们选择放弃乃至背叛自己的初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80年代的改革派知识分子甘阳。六四屠杀之后,甘阳流亡西方,曾在芝加哥大学求学,因攻读博士学位受挫而对西方充满仇恨。后来,甘阳赴香港大学任教,成为反西方的、民族主义的吹鼓手。他炮制出「打通三个中国伟大传统」的理论,希望被最高当局采纳。所谓「三个传统」,即孔子的儒家传统、毛泽东的社会平等的传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传统。然而,这三传统自相矛盾、彼此对立:毛泽东时代曾批判孔子,派红卫兵砸烂孔庙、发掘孔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对毛泽东来说则是修正主义、是叛徒。甘阳为了被中国政府宽恕并重用,匆匆献上「通三统」理论作为投名状,完全顾不上修补这些学理上一目了然的漏洞。近年来曾经红极一时的反对派名人如焦国标、艾未未等人也走上了「杀人放火被招安」的老路。
乔治·欧威尔在《动物庄园》中的最后一句话是:「窗外的动物们先看看猪,再看看人,又反过来先看人,后看猪,但他们再也分辨不出人和猪有什么分别了。」当反抗者变得跟反抗的对象一模一样,反抗还有什么价值呢?
让基督教保守主义像光一样照亮反对运动
那麽,中国反对运动的出路何在?中国如何开启未来的民族转型之路?中国家庭教会以及在家庭教会中成长起来的基督徒保守主义者、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近年来,加尔文神学及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进入中国城市新兴教会。加尔文认为,神学是一种「实践科学」,他自始至终都致力于从神学的视野思考法律和政治观,他比马丁·路德更积极地强调上帝的律法对基督徒生活和公共政治的指导和约束——一切拓展人类自由的事业方面,教会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基督教的重要价值是「让被虏的得自由」。德国神学家莫特曼指出,「上帝」这名字应许从罪恶和死亡中得自由是我们无尽的自由。从政治性的奴隶制度「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在旧约传统中占据核心地位;被钉十字架的基督复活,进入永远自由的国度,在新约传统中占据核心地位。基督徒相信基本的价值观,如人性尊严、人身自由、人权等,都是源自创造万物的上帝。自由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不能让这个宝贵礼物被独裁者无缘无故夺走。放弃自由,就意味着人忘记了人是上帝按照其形象造的;放弃自由,就意味着人玷辱了上帝赋予的「治理全地」的权柄。使徒保罗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作人的奴仆。」基督徒不能安于被奴役的状态,教会也不能成为政权的奴仆。
以改革宗信仰出发,教会必然是一种公共性的存在,个人的信仰必然是一种整全性的生活方式。归正信仰不主张采取「属灵」与「属世」完全对立的、一刀两断式的二分法,而主张基督徒既是天国的子民、又是地上的公民。信徒对教会有委身,教会对社会有责任。教会要成为抵挡和纠正错误的时代潮流的中流砥柱。教会具有独立和超然的地位,如果教会像墙头草一样随风而动,便背离了上帝的真道;如果教会成为政权手中的筹码,信仰那超越性的价值便无法持守下去。
在教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若干血的教训。比如在纳粹刚刚开始兴起时,德国教会假装没有看见纳粹迫害犹太人等罪恶行径,为「反正纳粹残害的不是我们」而暗自庆幸;当纳粹向教会伸出黑手时,教会已经没有招架之力,只好乖乖地臣服于希特勒的淫威之下。以生命殉道的潘霍华牧师严厉批评说:「我们的教会在这些年只为自己的存留而奋斗,好像这才是主要的目的,这样的教会没有能力成为世界的代言人,为人们讲出和解及拯救的话语。」他强调,基督徒不能单单安享上帝的恩典而对外面的世界闭目塞听:「由于基督承担起我们的重担,所以我们应当担负起同伴的重担。基督的律法就是背十字架,这也是我们要完成的任务。」
中国海内外民主运动陷入低潮,原因之一是:「民主」无法形成一种永恒性的信仰,它只是权力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只是诸多社会运行模式中「最不坏」的一种,它甚至比不上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更有号召力。反对运动需要更高的信仰提供意义和价值,基于基督信仰的保守主义价值观可以像光一样照亮反对运动。
从基督教中寻找力量和精神源泉的抗争者越来越多。刘晓波将基督教信仰当作精神支柱。早在80年代中期,刘晓波就从研读康德进入基督教文化,他认为:「中国的悲剧,是没有上帝的悲剧。」他在天安门运动之前计划出版的一本书,就名为《赤身裸体,走向上帝》。此书还未上市就被销毁。刘晓波在狱中最喜欢读的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传承傲慢自大的儒家人格,号称「内圣外王」;刘晓波是其中少有的、具有基督教「忏悔精神」的人。他从不认为自己是英雄或圣徒,而认为自己是「可耻的幸存者」。当他因《零八宪章》被中共判处11年重刑时,他在法庭上的最后答辩词名为「我没有敌人」;当他获知自己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时,他对前来探监的妻子刘霞说,这个奖是给「六四」受难者的。这种反抗者的谦卑,在中国反对派领袖中十分罕见。
刘晓波与90年代后期兴起的家庭教会保持着密切联系。当我所在的北京方舟教会受到警察骚扰时,他撰文加以声援,赞扬信徒们的非暴力抗争手段:「基督徒甘愿承受苦难的良知反抗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当人类必须面对被强加的暴政及其苦难之时,居然是受害者心怀谦恭而尊严的爱意,主动邀请加害者回到仁爱、宽容、理性、和平的规则中来。而神意的回归,必将通过殉难的持续累积(接力式反抗)和极端受难形式(被钉十字架)对施害者的灵魂构成的巨大压力。作恶者施暴的强度与受难者抗暴的韧性成正比,所谓基督教的『坚忍主义』,就是用基督徒承受苦难的毅力来对抗迫害者制造苦难的意志,用信仰给予灵魂的力量来抵抗恐怖暴力的肆虐。」
在中国历史上一以贯之的暴力冲突、改朝换代的模式之外,家庭教会的抗争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中国不能再发生一次毛氏革命,悲剧的重复就是闹剧;中国只能学习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独立革命那样的「革命」,并以此走出历代王朝更迭中人相杀、人相食的惨剧。刘晓波概括说:「无论遭遇怎样的不公正,基督徒的良知既不会诉诸于仇恨和暴力,也决不会屈从于恶法和权势,而是坚持用爱来融化恨,用善意来唤醒敌对者的良知,用徒手不服从来征服全副武装,直到良知者忍受苦难的能力消耗尽施暴者的仇恨,最终超越‘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参照南非成功社会转型(政治领域)的经验,可以想象,若没有浸润在基督教文明中的曼德拉和图图主教的不懈努力,若没有代表人间正义和人类良知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高速运转,横亘于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之间的暴戾之气,如何消解?若冤冤相报,这个国家永远没有未来。
另一位基督精神的实践者是2016年8月3日被判处七年半重刑的北京家庭教会长老胡石根。胡石根在「六四」后因参与民主党组党活动,被判处20年重刑,坐了16年牢。这一次再度被判重刑,刑期加起来可以「将牢底坐穿」。这一次判刑,检方将胡石根受洗的照片作为罪证之一,而罪名是「利用宗教力量反对党和颠覆政府」。
前一次入狱的16年当中,胡石根一直在苦苦思索中国的出路。在世俗政治的黑暗和人性的败坏中,他看不到任何希望。「我在监狱里,真的是对中国人陷入绝望。我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命题,叫『中国孬种』。很多人听了会不太舒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经过将近100多年的奴役,中国人把过去所仅有的一点刚强、勇敢、骨气,都给消磨了。尤其是经过这60多年的奴化教育,上上下下,几乎所有人,都变成服服帖帖的奴隶,而且甘心于做这样的孬种,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那时,我觉得不仅个人没有希望,整个国家都没有希望。」
一位报导中国真相的记者说过,光明不是由黑暗来定义的,而是由寻找光明的人来定义的。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胡石根惊讶地发现,有一批基督徒狱友和别人就是不一样,他们谦卑、忍耐、平安、喜乐。于是,胡石根就跟这些基督徒攀谈、交往,从他们那里听到福音,进而被上帝挑选成为基督徒。胡石根在《圣经》中发现了自己的名字:「上帝的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奇妙的是,并不是基督徒的父母亲,给他取名时让他的名字中包含了「柱石」和「根基」的双重含义。
第一次出狱后,胡石根成为北京一间家庭教会的长老,他在新兴城市教会中找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看到家庭教会的发展,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积极传福音,看到那一张张洋溢着神的荣光的脸,我又慢慢从绝望中振奋起来。我感到中国还是很有希望的,上帝正在中国施行奇妙的事情。这60年,对中国损害最大的,还不是这个物质财富上的损害,更多的是,是对人心的毒害、对文化的毒害。我们有必要通过福音化,来解决人心的缺失、文化的缺失问题。从而使得我们在争取民主化的过程中,能够赢取人心;在巩固民主化的过程中,能够凝聚人心。这就是福音化在中国的重要意义。」那几年里,胡石根将生命的重点转向传福音和建教会,但也没有放弃参与政治活动,他身体力行地将内在的生命敬虔和影响公共社会两者融为一体。清教徒时代的信徒就是如此,信仰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关系,上帝从来没有让基督徒在政治领域缺席。信仰不是政治之工具,信仰却不能外在于政治而存在。
胡石根如此描述对自己所在教会以及中国家庭教会的热切期待:「我希望我们这个小小的团契,能够在查经学习当中,通过祷告,通过分享,通过查经,不仅是在知识上了解神学,了解基督教,了解圣经,更多的是要把我们个人的生命、个人的生活,同主耶稣连结在一起。我们要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来,这样我们的教会就能成为一个主所悦纳的教会。我希望更多的家庭教会,现在也许会被称之为老底嘉那样的教会,通过跟主建立生命上的联系,来变成伟大的教会,在中国基督教兴起的时代中,来见证神的荣耀。」
中国并非没有未来,中国的未来不掌握在共产党手中,也不掌握在被共产党意识形态所毒化的、做着皇帝梦和总统梦的「当代洪秀全」、「当代孙大砲」手中,而掌握在刘晓波、胡石根等热爱自由、坚持公义的知识人和数千万「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的家庭教会信徒手中。
(Photo credit: Andrew121215 / CC BY-NC)
传扬论坛期待透过每篇文章激发更多基督徒思考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不断重新理解上主在这个世代的心意。 面对艰困的媒体环境与难以质疑、反省的教会文化,我们没有教派包袱,愿在各个公共议题上与大家一同反思。 为维持平台运作,传扬论坛每个月需要15万元经费,祈请兄姐关心代祷及奉献,与我们同行,并向更多人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