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短暂休兵的同性婚姻立法争议又起。基督教右派举起宗教自由大橥,主张同性婚姻事关基督信仰的危急存亡。支持同性婚姻立法者,则多半把宗教与不宽容划上等号,认为宗教理性不该涉入公共领域中。
其实,这一切恐怕如宗教学者凯伦.阿姆斯壮(Karen Armstrong)所言,误将团体间的敌对行为作错误归因,实是「现代社会把信仰变成了替罪羊」。纵使双方的激进份子看似二元对立,但其实彼此的相同处远大于外表的相异,二者都把这场立法对决看作是「宗教vs.非宗教」一场无解的文化战争。但这究竟更多是事实,抑或不过是迷思?
宗教自由诉求更有利政府立法
法学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面对美国本土基督教右派的护家运动指出,虽说少有男女在获得同性恋和堕胎的选择权上诉诸宗教理由,但以宗教自由作为诉求,其实更有利于自由派的主张,连带使得政府推动相关立法益发具有强制性。
但这需要先解决两个问题,首先,到底什么是宗教?哪些人或团体得以享有上述相关的保障?其次,到底宗教自由的人权诉求该如何经由法律加以保障?
前一个问题好解决。德沃金一方面援引天主教大公会议的声明,主张「无法想像任何对于何谓宗教信念的具说服力解释可排除以下这种信念:对于人生为何及如何有着本具客观重要性的信念」,另一方面,借着爬梳美国最高法院对于宪法保障宗教自由的解释文,指出「在这个国家,不教导人相信上帝存在的宗教包括了佛教、道教、伦理文化协会和世俗人文主义等等」,进而提出「宗教性无神论」的说法。
举凡任何人或团体,若秉持着「宗教性态度」,用超自然主义(supernaturalism)的信念,来看待自然和价值,认定他们背后具有先验的客观依据,不论是有神论或无神论,都理应被视为宗教。
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如同言论、集会结社种种自由,宗教自由既与人性尊严密不可分,便应受到政府立法加以尊重和保障。
「宗教性无神论」的宗教自由可以包括哪些?像是选择堕胎或选择与同性结离的决定,都涉及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v. Casey一案三位大法官的意见书所言的,「凡是最私密和最个人选择(即最攸关个人尊严和自治的选择)的事情,……,此种自由之核心在于人有权利自行界定其存在概念、意义概念、宇宙概念和人类生命之谜的概念」,理应被视为是宗教性信念,获得政府立法加以保障。
政府的合理界限在哪里?
然而,自由不单是个人的事,也关乎旁人,不只是项权利,更是项义务。说「某人有权获得X」,意味着其他人对此负有相对的义务,这往往意味着,就消极面来说,他人不得对某人获得X横加干预,甚至就积极面来说,他人理应协助某人得以获得X。宗教自由也不例外。
惟回顾宗教战争及暴力的相关历史,宗教自由作为人权,如同其他受到保障的自由一样,很可能会对他人其他权益造成危害。正因为如此,在一个多元宗教的社会中,「政府究竟该如何立法保障宗教自由?」这个问题相较于前者,困难来得多得多。
现今社会不可能认可以宗教自由为名进行杀戮,像日本地下铁沙林毒气事件,或使用有碍健康的毒品,如美国原住民教会在宗教仪式上使用致成瘾药物佩奥特碱(peyote)。宗教自由若不想成为失控的火车头,亦理应在「合理界限」内加以规范。所以〈欧洲人权公约〉补充:「表现个人宗教或信仰之自由仅在以下情况受限制:不符法律规定者,有违民主社会中表现公共安全之利益者,有违公共秩序、健康或道德者,有违他人之权利与自由法。」
政府究竟如何订出「合理界限」,到什么程度算跨越红线,是对宗教自由直接或间接的侵犯?这件事无法不证自明,也不那么黑白分明,是个需要法律社会学详加诠释的概念。
土耳其及法国不准许穆斯林妇女在公开场合穿戴全罩式长袍;瑞士藉全民公投禁止在国内修建伊斯兰教宣礼塔;中国强拆教堂十字架;台湾甚至有人主张宗教徒个人或团体进入校园担任义工,不得配戴或穿着表现宗教认同的象征性物件,凡此种种容或会被视为是假「合理界限」之名,行「侵害宗教自由」之实。
而近来在同性婚姻修法过程中颇受关注的,政府是否不得资助或立法禁止拒绝同性家长收养的天主教等相关机构,这算不算是?却犹待斟酌。
大多数谨守政教分离原则的国家,多遵循二项原则来行事,首先,禁止政府为特定宗教背书;其次,禁止政府限制履行宗教之自由。前者禁止政府积极参与并涉入宗教事务,以防止宗教为政府所利用;后者禁止政府以国家认同和公民意识为由,来消极打压如同美国宾州亚米胥(Amish)派及锡安山新约教会等具强烈分离意识的宗教。
但这件事说来简单,要落实却不容易。原因在于,第一项要求和第二项要求,似乎经常相互抵触,比如尊重A宗教自由,豁免其某项公民义务的同时,像是耶和华见证人出于信仰的缘故得以拒绝当兵,似乎就对无法享豁免的其他人构成了某种不公平待遇,仿佛是政府己经选边站了。
平等,就是要一样,这是把两刃剑,有时它可以有效地去除歧视;但有时反而被用来强化歧视而不自知。政府相关法令对不同宗教信念会带来迥异的冲击,硬要他们遵守相同的公民义务,就是一个要不得的实例。犹有甚者,这可能包藏一个隐而未显、打造国家神话的祸心,即借由国家法律建构凌驾于不同宗教认同的世俗公民意识,纵容政府只要找到看似中立的托辞,就可以想禁什么便禁什么。
容许破例并保障所有人权利
德沃金很明白这点,因而进一步区分二种对宗教自由人权的法律保障模式,其一为「伦理独立权利」(rights of ethical independence),另一是视其为「特殊性权利」(special rights)。「特殊性权利」,如同公平审判、言论自由等,受到极强的保护,或是严格到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不得加以侵犯,或者,除非有着「迫切正当事由」(compelling justification)等缘由,像是某种不实的谣言会造成个人权益或社会「清晰分明且迫在眉睫的危险」等,否则绝不允许加以侵犯。
宗教自由若要被视为是「特殊性权利」,那么政府在立法时,乃至于法官在审理时,便不得不对何谓宗教进行某种实质内容的审查,判断某信念是否归属于某种可加以辨识的更大且一致的信念系统与人生观。
但政府究竟有没有能力或适不适合担任「判教」的重责大任?其决断又是否可以真的维持价值中立?不免令人质疑。
若宗教自由是一种「伦理独立权利」,那么宗教就必须愿意服从理性、无歧视和对各宗教相同尊重的相关法令,相对的,政府在立法上便不得以涉及实质内容的价值选择(认为某种生活较为可取),来立法制定攸关宗教自由的公共政策。这意味着,「立法机构在打算禁止或限制某团体的某种活动时,须先弄清楚该团体是否把该活动视为神圣义务。」
若果是,那么政府便必须考虑,基于「同等尊重」是否该加以豁免或给予优惠。这里需要考量的,不是原则上宗教自由是否都不得加以侵犯的问题,而是实质上容许破例对政策所会造成的实际影响,「若是一个破例对一项政策无明显损害,那不批准该破例也许就是不合情理的」。
基于这样的法律框架下,在德沃金看来,不禁止因信仰因素拒绝提供同性家庭领养服务的宗教性机构,甚或提供政府资助,是可行的。但这样的施政有附带条件,就是政府同时有责任设立充足的其他领养机构,以致同性家庭的收养权利不因而受损。
台湾现阶段同性婚姻修法的正反对决,让平时不受重视的宗教自由转变成为舆论聚焦的当红炸子鸡。或许趁现在把宗教如何自由的人权法律规范讲清楚说明白,是福非祸!
(封面相片来源:American Life League / CC BY-NC)
传扬论坛期待透过每篇文章激发更多基督徒思考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不断重新理解上主在这个世代的心意。 面对艰困的媒体环境与难以质疑、反省的教会文化,我们没有教派包袱,愿在各个公共议题上与大家一同反思。 为维持平台运作,传扬论坛每个月需要15万元经费,祈请兄姐关心代祷及奉献,与我们同行,并向更多人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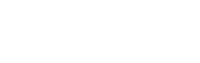
《宗教自由非积极自由》
论坛所刊登陈文姗教授所撰「宗教如何得以自由?」一文,笔者有部分回应与补充。
对于自由权利,哲学家如以撒·柏林或约翰·格雷等,曾将这个概念理解为「消极」与「积极」两种样貌,如果我们理解「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不同,将有助于跳脱宗教自由的误区。消极自由乃是个人或社群抵抗其他个人、社群乃至国家等外力之不当干预与压迫,而积极自由则是个人或群体对于达成其社会想像理想型态的追求。所有的自由权利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特质,但如果我们倾向以积极自由来理解自由权利的话,很可能会导致民主另一个重要的基础原则,「平等权利」受到压抑或消灭。
※宗教自由是消极自由,或积极自由?
在民主社会当中政教分离原则不仅是为了促进宗教宽容,进而消弭大规模与暴力形式的宗教冲突,也是为了保障不同宗教或信仰的人们得以抗拒外力干涉其内部的宗教信仰及活动的实践。
如果我们把宗教自由视为积极自由,我们可以预想到,各种宗教就会透过各种方式与管道去制定符合各自教义的公共政策与社会制度,其中强烈排他的一神宗教,可能无法容忍其他宗教或思想的存在,而强制其他宗教或无神论者依据其教义去生活。然而,这样就违背了平等的宗教自由的概念,因为宗教自由应当是每个人都能享有拒绝外力干涉的自由权利,但以积极自由的形式去理解反而使得部分人的宗教自由受到限制与侵害。因此为了避免宗教自由反过来侵害个人的信仰,我们应当理解宗教自由为消极自由,主要为被动抵抗外力干涉的自由权利性质。
※宗教自由是否扩及宗教团体的事业体内部自治?
陈文姗教授文中提及关于宗教背景的儿少安置收容及收出养机构是否可以依据宗教教义拒绝提供同性伴侣家庭服务?而政府是否可以对这类的歧视行为加以处罚?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加以介入,违反歧视原则之儿少安置收容及收出养机构,情节重大者更应该处以停业或撤销立案之处分。这边除了儿少安置收容及收出养机构我也希望提出宗教团体设立之私立学校来做为说明。
无论是私立学校或是儿少安置收容及收出养机构,其基本上都是政府特许民间经营的事业。私立学校的设立目的是为了促进就学权利以及教育发展的教育事业;儿少机构则是以儿童福祉为优先的社会福利事业。我们应该理解在学校及儿少机构当中,利害关系人不只是只有兴办或资助事业的宗教团体跟政府主管机关,至少仍包含就读之学生及受安置儿少,甚至还包含在这些事业体中工作或生活的工作人员。
如果宗教团体兴办资助之私立学校及儿少机构可以因为学生或收养申请人之性倾向或其他原因拒绝提供服务,将可能导致学生及受安置儿少之宗教自由受到侵害,特别学生及受服务儿少,本身对宗教之认同不应该由学校或机构背后的宗教团体决定,应该预留这些学生及儿少未来之选择权。因此学校与儿少机构即便由宗教团体兴办或资助,仍应以教育或儿童福祉为专业考量,尽可能排除宗教团体本身教义或所其主张之「宗教自由」干涉或思想灌输。如果我们将这项专业的考量扩及其内部工作人员,包含学校教职员或机构行政或服务人力,我们甚至可以得到私立学校及儿少机构本身应该具有一定程度不受资助之宗教团体干涉的专业自主性,这也是政府未来应该加以保障跟介入之处,未来应在宗教团体法与相关法律中以规范。
※小结:宗教自由贵在自律与反思
在2013年时基督宗教大学联盟即以宗教自由与大学自治之名,声明将对抗「性别平等教育法」,直接反对多元成家三法草案并捍卫其以宗教教义行歧视的自治权利,在2016年辅仁大学与中原大学也针对同性婚姻民法修订案表达声明,即是很明显意图将宗教自由理解为积极自由,导致平等权利可能受到侵害的最佳例子。
在我们讨论宗教自由时,不应该限于讨论如何实践自己的「宗教自由」,应该顾及所有人是否可能在这样的权利理解与实践中受到平等对待或是否产生损害,而不能实践其个人及社群内部之宗教活动。个人认为宗教团体严格自律与反思,并且愿意理解不同宗教或价值之人权的生命与实践,才是有利于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原则的最佳理解。
看到以上这篇回复的文字,觉得蛮感动的。笔者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只想说获益良多,且佩服这种讨论过程。
公共讨论贵在理性且仔细地陈述自己的想法,无论观点是否相同都无妨。
好几次在论坛里面看到的回应,有时候直接就拿没有论述的[宣称]来回应对方,其实不是很负责。
这次难得看到这么长篇幅,足为一篇文章的实质回应,不仅对本讨论非常有助益,对日后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诸多面向也都提出具体的观点。
说真的,基督徒社群的讨论,当如是也。
对于楼上的讨论,作为作者,我有几点回复,
1.请勿误植他人姓名,是珊,非姗,这是对人的基本尊重。
2.有关于本文,实重在引介德沃金的思想,以便突显目前台湾同性婚姻立法过程中对立双方论述的盲点,希望可以有助于打破僵局。这未必是我个人对宗教自由如何保障其背后的法律架构最终的定见。这点从本文不敢居功,不断提到德沃金,并使用直接引句引用他的原文中译,便可清楚。任何算得上公允的评论,不可能略过德沃金的见解。然而,楼上只字不提德沃金,不知是对德沃金思想不熟悉,或是,误读了本文用意。
3.楼上既引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便可知这不过是思想上的方便区隔,并不代表二者没有重叠处,更不意味着在实际上总能把某一自由的行使分门别类地画定作是消极的抑或积极的。与此相关的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区分,业以因此受到不少批判,特别是涉及到制度设计的问题。
4.既便不深究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区分的适当性问题,楼上以为宗教自由若理解为积极自由会带来对平等保障的危害,因而宗教自由只得理解作消极自由。这样的看法并站不住脚。即便宗教自由被理解为积极自由,其对平等保障的危害只是可能,而非必然,而政教分离下的宪政国家可以如何在人权法律架构下保障不同宗教行使其积极自由,正是德沃金所要苦心论述的。
5.承上,若不深究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区分的适切性,楼上认为若把宗教自由理解作消极自由,便不会引发宗教不宽容,乃至政策制定上不平等的问题,这点也不是不证自明的。到什么程度算是「外力之不当干预与压迫」,其实有待进一步论述。
6.综合45,认为借由区隔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便可以解决在现阶段同性婚姻立法上有关于宗教自由所引发的争议,实是错误的期待。
7.本文中有关于领养机构的种种讨论,并非本人意见,正是德沃金根据美国有关于宗教自由相关争议所作出的建议,「若是一个破例对一项政策无明显损害,那不批准该破例也许就是不合情理的」,这样的作法附带着一项要求,即政府同时有责任设立充足的其他领养机构,以致同性家庭的收养权利不因而受损。这反映的是德沃金的自由派法学期待把宗教自由定位作「伦理独立权利」的法律制度性设计,并早就提过需作政策损害评估及政府理应保障其他人的权利。
8.领养机构与宗教办学二者所面对的实际损害问题及相关配套保障并不相同,楼上将二者合并来谈,不能清楚区分二者的性质,并不是个好的做法。而且,很有可能犯了打稻草人的谬误的嫌疑。这是所有逻辑谬误中,最要不得的一种,因为它往往是出于故意而非无心。希望这样的厘清,可以避免其他人再犯类似的问题。
9.有关于楼上结论所言宗教自由的平等保障与政教分离原则,我己在「宗教,不宗教,这成了个问题」一文(https://weproclaimhim.com/?p=4900),有所论述,不再另行着墨。
我之所以愿意花时间作回应,是因为楼上的误读,其实反映了台湾同性婚姻立法正反方激进论述中典型对宗教自由的误解。反同者以为,宗教自由可保障其不受政府施政限制,挺同者误以为,宗教理性不得涉及公共政策的制定,这样的误解除了造成二元对立的激化,并无助于解决问题。德沃金另辟的第三条路,适足以厘清问题焦点,有助于同性婚姻立法的公共论述,这是本文写作的初心。
首先,陈文珊教授姓名之误植为本人疏忽,在此向陈教授道歉。
然而,在宗教性兴办资助的各种事业,纵然有其不同之性质与功能,但其实皆不应完全视为宗教社群之内部行为。如以儿少机构论之,儿少机构之设立,是属于国家特许委托民间团体之事业,其相关规定皆属于各地社会局处所管辖。换言之,这些儿少机构应该视同公权力对社会介入之延伸,是代替政府实践并履行对于儿童与少年权益之保障。
因此宗教背景、兴办或资助的儿少机构是否得以教义对性倾向之诠释理由,拒绝同性伴侣之收养申请而收养其机构之儿童及少年,应是非常清楚。基于儿少机构属于代替政府执行业务,自然应受政教分离原则规范,并尊重各利害关系人之利益。其中包含受机构服务之儿童及青少年对于未来信仰与价值判断、追求家庭与照顾之权利;还包含专业人力的基于专业的自主空间;最后也收养申请人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些行为者皆不应受歧视。
其中,儿童及青少年更是其中应该关注的无权者。一般来说,收养人提出申请后,可能经由社会局处及专业机构等程序媒合待出养之儿少名单,而自动省略对于特定收养人特质不予接受的机构,如此可避免申请人遭受歧视对待。但如果收养申请人各种条件皆评估完备,有受专业认可的教养能力,何以机构能不让儿童进行出养?国内受安置儿少人数皆少于收养申请人,但是孩童如果待在一个宗教背景、兴办或资助之收出养机构,机构基于宗教原因拒绝提供收出养服务配对,等于限制甚至剥夺儿童及少年得以出养的可能性,此不可不慎。
当然我们也许可以有更多制度上的设计改良可以避免这种情形发生。但是在资源与选择有限的状况下,我们该当如何进行判断,是否应该加以介入?消极与积极自由的界线与判准、侵害程度有应细谈之处,或者也可以想想在保障宗教自由的条件下,这些受服务对象是否也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权利侵害?即便我们没有谈及更多细节,但这不妨害我们讨论、理解宗教自由的界线。以上是个人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