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癌末的消息於上個月傳出後,國際人權組織和人權運動者極力奔走於歐美大國之間,期能透過國際壓力,讓劉曉波有離開中國就醫的機會。不管最後中國政府是否允許劉曉波能夠離開中國就醫,作為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國民主運動重要人物的劉曉波,都注定成為這個階段中國知識份子悲劇性的象徵。
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後到2008年,劉曉波長期從事關注中國民間的維權運動及民主運動。他最為世界所熟知的部分,主要是因為在2008年,他與張祖樺等人共同草擬《零八憲章》,作為中國知識界向統治者提出政治改革的主要訴求。
2009年,他因為遭到中共政權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而獲罪入獄。起訴書內文非常明確地指控其在2005年以來,不斷在國內外重要網路論壇當中批判統治當局,以及2008年《零八憲章》中訴求「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及「在民主憲政的架構下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劉曉波的入獄引起中國國內和海外的極大關注,也因此使其獲得201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從他獲獎到近日罹癌消息傳出前,他都一直受到中國當局的關押。
捨棄民族大義,追尋人性尊嚴
作為一位中國知識份子的異類,劉曉波在1980年代就以一個文化上激進的反傳統主義者的姿態出現。他最常受到批評的觀點就是他在1988年於香港接受《解放月報》的金鐘專訪時,所曾提出的「中國300年殖民論」。這段談話,常使劉曉波遭批評為「叛國賊」。
當時,金鐘是這麼問劉曉波的:「什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呢?」劉曉波回答:「300年殖民地。香港100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300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300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金鐘知道這段話可能引來的質疑,於是接著:「十足的『賣國主義』啦。」劉曉波則回答:「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註1)
事實上,當人們以國家民族大義質疑劉曉波對於中國的忠誠的時候,往往忽略一個重要議題,就是他自始至終的核心價值:人文主義或人道精神。一個強調個人尊嚴的自由主義者往往會有某種程度對於民族主義的反省,只是劉曉波算是比較激進一點的。
他反對中國傳統,主要是基於中國傳統數千年來,由統治政權建構的意識型態是在維護專制政治,完全無法發展出人道主義的精神。因此,才使得劉曉波在了解了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傳統後作出這樣的結論。在同一篇訪談中,劉曉波清楚地指出了,「現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論自由、法律至上。……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化與中國制度的區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註2)
因此,可以明確指出,他所提出「中國300年殖民論」的重點,並不在於「國家民族」本身,對他而言,統治者是誰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國家的整體制度是否符合「現代」的標準,而現代的標準,就如同他所說的,是「過人的生活」。因此,重點是生活在中國土地上、作為真正主體的「人」應該過「人的生活」。
他的人道主義價值,從他在2009年受審判時的法庭最後陳述全文中也可看得出來。他說道:「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所有監控過我,捉捕過我、審訊過我的警察,起訴過我的檢察官,判決過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敵人。雖然我無法接受你們的監控、逮捕、起訴和判決,但我尊重你的職業與人格,……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註3)
對他而言,人權和民主的信念來自於一個堅持:所有制度改革的訴求都是為了實現一個能夠保障人性尊嚴的理想國度。因此,所有替不義政權工作的人不過是「平庸的邪惡」罷了,不該成為追求理想國度道路上的敵人。
這樣的主張難道不是一種人道主義精神嗎?提出此主張的人怎麼會是「叛國國賊」呢?更精確地問,他「背叛誰」、「忠於誰」?難道忠於人民能算是叛國嗎?
有趣的是,從八九天安門到零八憲章事件,由於具有國際知名度和關注度,劉曉波曾有多次機會得到政治庇護,但他仍繼續待在中國國內,關注維權運動和中國民主化的運動。相對於此,那些批評他是「賣國賊」的許多人,有不少都是從中國統治當局的「官僚資本集團」中獲利的人。可見,這些口口聲聲喊「愛國」的人,其實正是「竊國者」,用黃宗羲的話來講,就是「藏天下於筺篋者」(把國家當作統治者的私有財物)(《明夷待訪錄》〈原法〉)。這樣的對比,豈不諷刺?
對於經歷過民主化洗禮的台灣人而言,《零八憲章》的內容可能沒有什麼特別的,因為其所提倡的政治改革主張,都是一個現代民主憲政國家所應該具備的基本條件(完全不用我們在這裡複述一遍)。然而,這卻象徵著天安門事件後,中國知識界再次期盼改革的呼聲。
1989年文化激進的劉曉波,到了這段時間成了留在自己所批判的國度內部,以溫和漸進的手段,透過支持維權運動,以及輿論影響力在民間尋求中國改革契機的知識份子。
中國知識份子的異類:試圖成為殉道者
劉曉波當前的處境,其實是自我選擇的結果。在他作出選擇之際,他也應該早已知道自己可能會有的下場。
余英時先生曾非常感嘆地指出,從1989年的民運之後,由於整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快速提升至全球大國的地位,使得中國這個「神州」出現了千古未有的「盛世」。然而,正因為這個因素,使得這個時期的中國知識份子快速地成為「識時務」的俊傑,拒絕對當前政局提出批判,不再替底層百姓請命。因此,他借用易經當中的「天地閉,賢人隱」來形容當時的處境(註4)。中國知識份子的集體噤聲,是令人感嘆的事情,但這也與統治政權統治策略奏效有關。
10多年過去了,中國不但在經濟實力上持續增加,其在全球的政治和軍事等影響力也與日俱增。余英時先生十多年前憂心的現象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有日益嚴重的趨勢。
當舉世正在矚目並期盼癌末的劉曉波,能夠在他生命末期的階段接受到更人道的待遇,與此呈現對比的現象則是:在中國的國內,絕大部分的民眾,由於受到網路管制的緣故,根本無從得知劉曉波其人其事。即便部分中國民眾得知了劉曉波其人其事,也仍有許多中國人和中國官方媒體的口徑一致,將劉曉波視為「叛國賊」。視其為「叛國賊」的理由非常簡單,就是意圖「煽動顛覆」締造當前大國「盛世」的統治政權。
傳揚論壇在前幾日的文章〈《天降》:中國能向天期盼什麼?〉中,作者即已清楚地引述相關的觀察和研究指出,劉曉波具有許多當代中國知識菁英「親基督教」的特色。然而,中國的知識菁英都想學當耶穌,卻不想像耶穌一樣永遠釘在十字架上。
在這一點上,劉曉波可能是少數較為不同的一位。他如同許多當前被關押在獄中的維權律師一樣,並沒有選擇「流亡」(儘管也有很多海外流亡的知識份子也是被迫流亡),更沒有選擇留在國內對政權「忠誠」,而是選擇了一條最辛苦的道路:留下並「反抗」。只是這反抗是用溫和的手段來反抗。
早在1980年代末期,劉曉波在談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時候,就提出,中國中國知識份子的「唯我獨尊」特色,讓他們缺乏自省,也只會想要「聖化」自己。
他寫道:「不信上帝或沒有上帝的人,必然是『唯我獨尊』的狂妄者,中華民族正是如此。特別是中國的知識份子,稟賦了儒家的『人格至上主義』的遺傳,讀了幾本四書五經便飄飄然如入仙境。……在中國的歷史上,幾乎找不到一本類似西方的《懺悔錄》那樣的書。……西方人的『原罪』感使他們經常面對內心世界的邪惡、軟弱和犯罪感,而中國人的『樂感』使之無法正式自己的內心真實。」(註5)
劉曉波在將近30年前對於中國文化下的人們缺乏內省能力的批判,以及其對於基督教文化當中獨自面對上帝並時常進行反省的元素的推崇,其實可能正反映了其拒絕追求自我聖化、卻又試圖提出抗議之聲的態度。
在2000年,劉曉波在寫給作家廖亦武(現流亡德國)的一封信當中,清楚地提到了在經歷了十多年對於八九民運失敗的反省後,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中國缺乏「一個道義巨人」,在此我們仍引用其文字:
「與其它共產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們都稱不上真正的硬漢子。這麼多年的大悲劇,我們仍然沒有一個道義巨人,類似哈維爾。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權利,必須有一個道義巨人無私地犧牲。為了爭取到一個『消極自由』(不受權力的任意強制),必須有一種積極抗爭的意志。歷史沒有必然,一個殉難者的出現就會徹底改變一個民族的靈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質。甘地是偶然,哈維爾是偶然,2000年前那個生於馬槽的農家孩子更是偶然。人的提升就是靠這些偶然誕生的個人完成的。不能指望大眾的集體良知,只能依靠偉大的個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眾。」(註6)
他所提到的「道義巨人」,所面對的都是一個龐大的壓迫體制,面對這個壓迫體制,只能寄望個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眾。或許是基於對八九民運失敗的這種深刻反省,他試圖在中國尋找這個可能成為犧牲者的「道義巨人」,尋找之餘,也給他自己一個期許。
現在被關押到癌末的他,以及在近一個月來所引起的國際迴響,都顯示了這段他在十多年前寫的文字所透露出的訊息:選擇留下與抵抗,即使可能成為政權壓迫下的犧牲者,但卻換來了中國的一位道義巨人。
劉曉波在文字裡提到「2000年前那個生於馬槽的農家孩子」耶穌,在當年所展現的,也是一個與世俗的成就觀相對立的精神:以無罪之身為世人的罪「代贖」(atonement)。「代贖」是與人間常理相違背的「逆理」:明明自己沒有罪,卻要將自己投身在為有罪者犧牲的歷程中。這位「道義巨人」,正需要具備這樣的特色。
「大國崛起」下的兩種生命價值
2008年是中國「大國崛起」的重要指標年,這年,奧運會在北京盛大舉辦。劉曉波等人甘冒大不諱,居然在這時候發佈《零八憲章》。這兩大現象背後所展現的是兩種生命價值的對立:「大國崛起」所代表的是強調經濟展、國家繁榮至上的國家主義與發展主義;民主運動者所代表的則是追求一個更能保障人性尊嚴的國度。
這讓我想起,德國法蘭克福學派重要的心理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在他晚年(1976年)發表的成熟之作《所有或所是?》(To Have or To Be?)中所提到的重要觀點。佛洛姆區分了兩種生命的價值:一種是「所有」(to have)的價值,也就是強調透過一個人所擁有的財產來界定他的價值,例如:他擁有的社會地位、財富或權力等;另一種則是「所是」(to be)的價值,也就是強調透過一個人生命的本質來界定他的價值,例如:他的人格特質裡面有正直、誠信、慈悲、慷慨等。
佛洛姆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家,對物質主義抱持批判的態度。他認為,西方社會的精神過度受到資本主義精神主導的結果就是,強調「所有」的生命價值遠遠超過強調「所是」的生命價值。
如果以佛洛姆的觀點來檢視當前中國的話,則不得不令人感嘆:「發生過的事還要發生;做過的事還要再做。太陽底下一件新事都沒有。」(傳道書1章9節)
中國政權透過北京奧運,包裝了一個繁華昌盛的盛世,但盛世的基礎卻是到處充斥的物質至上的價值觀,社會的主流價值是:只要能夠賺錢發財,我管你什麼公平正義、人性尊嚴和環境保護?他們的價值是佛洛姆筆下過度追求「所有」的生命價值。
相對於此,仍有少部分為底層百姓請命的維權運動者和民主運動者,即使其努力未必被世人看見,但仍前仆後繼的為追求一個更公平正義的理想國度而奮鬥。他們的價值是佛洛姆筆下致力於追求「所是」生命的價值。
在《所有或所是?》的第七章,佛洛姆明確指出兩種精神的對比在西方社會的展現。「基督教的英雄是殉道者。……異教英雄的目的是征服,是戰勝,是毀滅,是掠奪。……殉道者的性格特質是活生生的生活,是給予,是分享;英雄的性格特質則是佔有、剝削、強迫。」基督教精神,儘管各種教派各有分歧,但卻有一個共同的信念:「相信耶穌基督是救主,他為了愛他的同胞而捨身。他是愛的英雄,沒有權勢的英雄,他不用武力,他不想統治,他不想『擁有』任何東西。他是存在(being)、給予與共享的英雄。」(註7)
劉曉波作為中國當代知識界、民主運動人士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其下場幾乎是悲劇性的。然而,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來看,成敗從不是從現世的表象所決定。基督教信仰的最好典範耶穌所代表的精神就是「殉道者精神」,殉道者精神是「給予」。
短期之內,以「佔有」和「支配」為主的大國崛起精神似乎仍將主導中國。然而,以「給予」和「分享」為主的「殉道者精神」卻會喚起千千萬萬的理想主義者,在歷史的長流中逐漸取得主導地位。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馬太福音5章11節)劉曉波注定要成為此世的悲劇人物。但他的悲劇,卻可能為中國成為尊重人權的國度換來契機。
註:
- 劉曉波、金鐘,1998,〈文壇「黑馬」劉曉波〉,《解放月報》十二月號。
- 同註1。
- 劉曉波,2001,《我沒有敵人》。台北市:捷幼出版社。頁i-v。
- 余英時,2000,〈「天地閉,賢人隱」的十年〉,《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61期(2010年10月號):頁36-38。
- 劉曉波,1990,《中國當代政治與中國知識份子》。台北市:唐山出版社。頁55。
- 劉曉波,2000,〈劉曉波給廖亦武的信(2000年1月13日)〉。
- Erich Fromm著,孟祥森譯,1994,《生命的展現:人類生存情態的分析》(To Have or To Be?)。台北:遠流出版社。頁166-167。
(封面相片來源:kunshou / CC BY-SA;中國政治異議人士劉曉波因為起草《零八憲章》入獄,於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然而,由於其在獄中,未能前往領獎。圖為當年頒獎典禮現場,一把空椅子是為這位獲獎者而留。)
傳揚論壇期待透過每篇文章激發更多基督徒思考信仰與社會的關係,不斷重新理解上主在這個世代的心意。 面對艱困的媒體環境與難以質疑、反省的教會文化,我們沒有教派包袱,願在各個公共議題上與大家一同反思。 為維持平台運作,傳揚論壇每個月需要15萬元經費,祈請兄姐關心代禱及奉獻,與我們同行,並向更多人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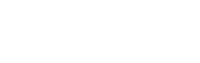
天地未閉,賢人沒隱,「教會」就是那正日漸成長茁壯的「道義巨人」!
時候將到!隱喻中的「巴比倫」將在沉靜中默然傾倒!
當代教會的確應該以那個「道義巨人」來自我期許,組成教會的人有自省和道德勇氣同樣重要。唯有放下自我中心才有這個可能。
近日在香港發生的事, 令人心情很沉重. 謝謝你的分享.
龔老師:謝謝。寫完這篇文章,以及這幾天香港的事情,我的心情也非常沈重!只怕這個政權愈來愈難纏了!